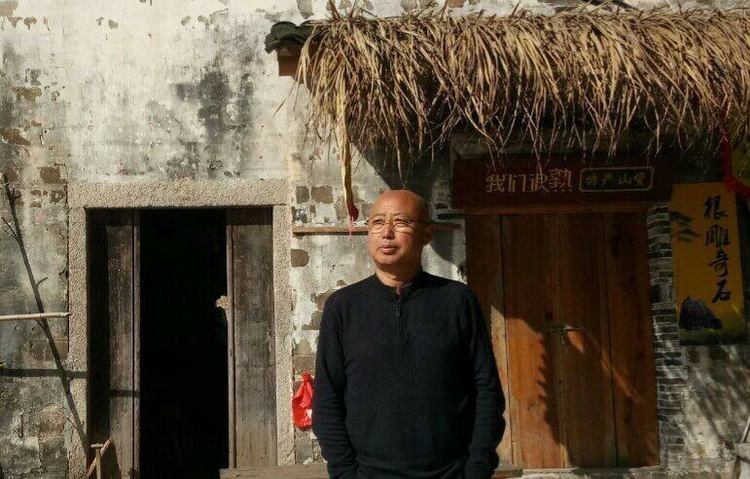好多年了,基本风调雨顺,人真得没有饿着。这跟我小时候很不一样。人灾不说了。我只记得那个时候,几乎每年都有自然灾害,尤其是旱灾。那时,乡村的小道上,村庄的小巷里,随处可见一手拿着饭碗,或者端着瓢子,另一只手里拿着要饭棍子四处讨逃荒要饭的人们。
“民以食为天,靠天有饭吃。”祖上一辈辈的都是靠天吃饭的。天旱时,尤其是连续干旱时,大地龟裂,草木枯萎,人们的吃水都成了问题……这时,村里的老人们开始张罗祈雨……杀猪、置酒、备香,一番准备之后,在村头建起祈雨坛。但见“玉皇大帝”坐镇,“雷公”,“电母”,“风婆”,“雨师”,“四海龙王”全到。人们成群结队,在祈雨坛下磕头烧香,拜天,拜地,拜菩萨;求云,求雨,求甘露……
这个时候,人们把所有的注意力转向天空。这个时候,天上除了旺毒地悬在那里的日头,整个的空空的。那些跪在烈日下,晒的满头大汗的人们,看起来距离天地很近。这个时候,“雨师”抬头看天,头顶偶有小鸟飞过,“雨师”点燃香火,开始把香言说。这个时候,所有的人们在言说,上天仿佛也在言说……那都是些半隐半显地言说。继而,人们看到天上忽而飘来几块云彩,忽而下几个雨滴,忽而又云散雨收……
时光如梭,天翻地覆。但每当回想起这些情景时,我印象的底片上总有一抹挥之不去得影影绰绰的云悬浮在那里。而且,那云时不时地会于时光地转换中,让我感受到一种之于天地万物牵一动百地颤动和某种基于生存论意义上的诘问,以及由此滋生出来的某些具有自然法则的那种内在神秘规律之于生命的忧伤。
十年前的一个冬雪之夜,我与嘉鸿兄在埠后村刘洪涛家围炉相聚。那晚,下着雪,飞舞着的雪片借着灯光一片一片的轻轻地打在院内初开的蜡梅花上。那腊梅花与雪花好像是约好了的,它们在那棵高过屋檐的腊梅树上,不断地纠缠着……
那个夜晚,我们也像雪花纠缠腊梅样地环绕在火炉旁。宽敞的平房里,大家围坐在以火炉为中心的不锈钢方桌周围,品着主人用雪水沏成的菊花茶,喝着主人自酿的菊花酒,听着主人用二胡演奏的《二泉映月》……从那个夜晚开始,我结识了刘洪涛,一眼发现了那种未被庞大社会机器与物质系统淹没的真诚。
刘洪涛讲义气,易激动,善交友,很有才。他跟我提起最多的,是他的老父亲传下来的名人字画,以及与那些字画有关的故事。他告诉我说,当年他父亲手里的那些名人字画,大多是从河南沟头村,他的一个舅老爷那里得来的。他的那个舅老爷姓孙,人称孙老爷。孙老爷是那一带的传奇人物,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记得他。前天,我和嘉鸿兄在东篱居与刘洪涛小酌时,又提起了他。
孙老爷原本家境一般,意想不到的是,他在自家耕地里种地时,一镢头改变了他的命运。因为,那一镢头下去,竟刨出了十八缸银子来。孙老爷便用这些银子大兴土木,盖起了远近闻名的孙家围子。
孙老爷有两个爱好,一是收藏字画;二是打猎。
孙老爷打猎很上瘾,几乎每天都要带着猎枪出去兜一圈。有天下午,孙老爷转遍了整个沟头南岭,却一直没有发现猎物。他有点累,坐在一草垛旁休息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醒来时,睡眼惺忪的他,看见一只黄鼠狼。那黄鼠狼很是奇怪,它骑在一只野兔的背上,正悠哉悠哉地从他眼前经过。孙老爷立即起身,迅疾开枪。那黄鼠狼和野兔立马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孙老爷喜出望外,很是开心。但是,当他带着猎物往家走时,很远就看见家里来人找他了。家人说:“不得了啦,奶奶一会昏迷不醒,一会说胡话,您快回去看看。”孙老爷顾不了许多,赶紧跑回家。回家后,发现老伴坐在床上浑身发抖,并且断断续续地说着一些含糊不清的话。孙老爷仔细听了听,大意是:外甥来这儿走姥娘家,出去遛马来,被你打死啦。
孙老爷一想,马上明白了过来。他立刻找来洋油和辣椒粉,然后提起家中的板斧,带着猎狗,赶到村子西南角那棵老槐树下。他挥起斧头,向树干砍去。几斧头下去后,树干上出现一个空洞,孙老爷把辣椒粉洒进树洞,然后浇上洋油,点起火来。不一会,从树上跳下一只三个爪的黄鼠狼。随后,又有黄鼠狼接着往下跳,总共跳下十二只。这些跳下树后的黄鼠狼,被等在树下的猎狗,一只一只的全咬死了。
之后,孙老爷赶回家中,见老伴已经好了。但是从那以后,北边村庄里那个看病很有名的瘸子看病不灵了。又过了不多时日,孙老爷的孙家围子起了一场火。那场火谁也说不清火是怎么起的。那天风势很大,整个孙家围子被那一把火毁了。
这个故事,我和嘉鸿兄多次听刘洪涛讲过,已经记在心里了。但每次和他小酌时,他都要讲一遍,每次我们都喜欢听他讲,直到听他讲完。因为他讲这些故事时,是非常认真的。每当听到这个故事时,我童年记忆里那个大岭上和我家东面那条小河沟里的那些密密麻麻、活蹦乱跳的小虫子和飞在头顶的小鸟、游动在水里的鱼虾,它们像一波波从遥远的天际间吹来的暖流,一波波地把我包围。在那里面还有老牛在河边对着日头啃草的声响,有我最喜欢的那条大黄狗看到野兔时紧追不舍的影子,有我家那只狸猫在阳光下伸开前肢打着呵欠的懒散样子……继而,伴随着这股暖流,孙老爷那个走远了的影子,又在洪涛弟的叙述中一次次来到我的眼前。
孙老爷因为那一镢头下去,刨出十八缸银子来,发了家。后来,又因为一把火,毁了整个家业……在刘洪涛这里听他讲孙老爷的故事时,我的脑海里总会一次次地闪过过往大旱之年的情景……继而联想被孙老爷烧死的那些黄鼠狼,以及那个突然看病不灵了的瘸子和那些跪在烈日下祈雨的人们……
每当这个时候,总有一首童谣在我的耳边回响:
小家雀,抖抖毛
拉着棍,抱着瓢
要了饭,喂小猫
小猫喂大了,拿个老鼠就罢了
……
听着,听着,我竟有点恍恍惚惚了起来,我感觉我自己仿佛和“小猫”、“老鼠”、“黄鼠狼”、“猎犬”处在一个相互贯通的一个大一时间的本体里面了,并且一时很难走的出来……那里面,孙老爷开的那一枪,孙老爷往树洞里撒的辣椒粉,树下被猎狗咬死的黄鼠狼,看病不灵了的瘸子,被一把不明之火烧光的孙家围子,旺毒日头下祈雨的人们……那是一团分不清你我的纠缠不清的存在!它似乎在告诉我,这里面所表明的一切,那也许是远远超出我的认知的另一种尺度。我分明感觉的到,在这种尺度的每一条细微的刻痕上,都驻留着许多数也数不清的,与我们的生命紧密链接着的,一种饱含着之于整个时空中的那种有着鲜活的生命意味的存在。这种存在在永无停息的宇宙空间中,一次次的持续演绎着一种牵一动百的,让所有存在了的事物不可或缺的,那个既定版本上的来来往往。
这些生命中的来来往往,常常于一件看似平常的事情里,就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就有可能消磨掉一个人的一辈子。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正在消耗着人的岁月,那些看似很小的事情,到底有多大是谁也说不清楚的。这里面有许多细节被我们忽略掉了。这里面,因为一只小虫子的夭折,因为一朵花的凋谢,因为一条狗的死亡,因为一条河流的改道,因为某一个事物的莫名消逝,而让整个大地颤抖了。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有着一个个真实存在着而又不为人们所察觉的,一个个事关人的生命存在和延续的惊心动魄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