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沂蒙
临沂同城
——记忆沂蒙

昨天上午,姨家表妹给我家送来一小包煎饼。煎饼呈灰黄色,很小,小的如同高压锅盖样大小。表妹说,那是她把小麦、黑豆、核桃磨成糊糊后,在家用小鏊子烙的。
表妹已不是第一次给我家送煎饼了,从前年春天她在家开始烙煎饼时起,我家就吃上了她烙的煎饼。表妹烙的煎饼不是用于卖的那种。如今市上卖的煎饼大多是机器加工的,又柴,又硬。表妹烙的煎饼很薄,薄如宣纸,软和,好咬,且能吃出小时候吃到的那种感觉来。而且,由于表妹在煎饼中加了黑豆和核桃,比起小时候吃的高粱、地瓜煎饼,味道和口感上都好了许多。
吃这煎饼时,我想起年轻时与同事去南方出发时的一件事。那是在郑州去广州的火车上,晚餐时,我跟同事在火车座位上打开包裹,拿出自带的煎饼,卷上榨菜和香肠,一起吃了起来。这时,邻座的两个南方人投来一种疑惑不解的目光,他们窃窃私语时,传到我耳朵来的是:“他们怎么吃纸呀?”。那个时候我没想别的,只是觉得邻座的南方人有些少见多怪了。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日新月异,馒头,大米早已成为主食,但在人们的生活中,依然少不了煎饼。近几年来,我与画家嘉鸿兄开车外出采风时,也是带着煎饼出去的。当我们在高速路服务区拿出煎饼时,依然有人感到好奇!但这却更能让我感受到之于煎饼的那份永远割舍不掉的特殊感情!尤其,在黄土高坡和云贵高原,当我们在山野的路径上,用煎饼卷上大葱时,感觉更是如此。
煎饼的起源有很多传说,流传最广的是诸葛亮被曹军围困突围后把锅丢了,没有了做饭的工具,诸葛亮就让士兵将铜锣放在火上,用面加水和成浆糊抹在铜锣上,于是就有了煎饼。但考古证实,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就已经创制烙饼的陶鏊了。显然,这个传说即便属实,也并非煎饼的起源。
煎饼对我而言不仅熟悉,可以说,我就是吃着煎饼长大的。小时候,在沂河以东姥姥家村庄居住时,由于那里地处丘陵地带,盛产地瓜,地瓜煎饼就成了那个村庄人们的主食。春节前,各家各户早早地用大瓦盆泡上瓜干,然后,用石磨把泡透的瓜干磨成糊糊,待发酵后,便在锅屋里用生铁鏊子和柴禾烙起煎饼。
烙煎饼,是春节前,沂蒙农村“办年”时,占用时间最长的一个重要事项,一般节前头半个月就开始了。但凡能推动磨的孩子,都要跟大人一起推磨。磨好煎饼糊糊后,孩子们就解放了,剩下的那些活,基本上都是母亲们的事。烙煎饼,一般在家中偏房的锅屋内。母亲们支好鏊子,用油褡子擦好鏊面;之后,在鏊子下面用柴草生火;然后,用勺子舀上煎饼糊糊,再用木制的煎饼耙子,在鏊面上拖着煎饼糊糊顺时针旋转,待把煎饼糊糊摊满鏊子后,再用煎饼耙子把面疙瘩抹平,不一会就出来一张黄灿灿的煎饼了。
在这个过程中,整个村庄被一缕缕蓝色的烟雾笼罩。这时,如果刮来一阵旋风,村庄的天空会出现一根盘旋而升的蓝色烟柱,那烟柱夹带着一股淡淡的烟火味,把整个村庄的烟雾向着天空收拢。继而,伴随而来的,是一波波源于大野的清新空气的进入。那空气从村庄的四周被吸纳了过来,它们丝丝缕缕地进入了每家每户的过道,深入到每家每户的锅屋……
锅屋是低矮的,被烟熏黑的锅屋门口,更是低矮。烙煎饼时,个高的母亲只得弯着腰进去。村庄的房屋太矮,人也是紧贴着锅屋内的地面的。这个时候,母亲坐在土搭地面上的一把干草上,弓着身子,点上了柴禾……这是一种天性使然的状态,这个画面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一种最为原初的印象,这种完全来自于我的生命印象中的原初造型,其中的感觉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我曾试图像画家那样,用我的文字为母亲描绘一幅画像,但我发现这个“像”实在无法画出固有的原本。那是新年就要到了的时候,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又要长出一岁了,正在烙着煎饼的母亲,心里充满了喜悦,那喜悦中有期盼,有憧憬,背后亦有生活中的酸楚,更有一些我永远读不懂的东西……就这样,连续十几天下来,家中的大缸里都盛满了煎饼,那煎饼,足够一家人吃好几个月的。
平常时日,母亲也是那样。记得我小的时候,天蒙蒙放亮时,母亲就起床了。刚刚睡醒的我,在床上能够清晰地听到母亲窗外推磨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很沉,很慢,每一步都使出很大的力气……母亲的脚步停下来后,紧接着,又传来母亲用勺子往盆里刮糊子、刷磨、抱柴禾和进出锅屋时的声响。待我起床后,母亲往往都把煎饼烙好了,一大早,我就能吃上母亲亲手烙的那个依然散发着锅灶余温的香脆可口的煎饼。
煎饼薄而干,易于保存。我在郭家哨联中和沂南十二中读书时,一直都是背着母亲给我叠好的煎饼和炒好地装在“红糖瓶子”里的腌菜一路走来的……
沂蒙一带用于烙煎饼的粮食主要有地瓜、玉米、高粱、小麦、谷子等。过去,在这里,烙煎饼是每个女人都会的活:“拙煞的木匠会打材,拙煞的老婆会做鞋,最拙的媳妇也能把煎饼烙出来”,是在沂蒙地区流传很广的一首童谣。因为煎饼,人们还杜撰出了许多与煎饼相关的故事。如“一大户人家,老爷和夫人得急症突然死亡,撇下小老婆和闺女黄妹子。老爷在世时,把闺女许给粱马为妻。但粱马家境已经败落,当家的小老婆想让黄妹子另嫁他人,多得些彩礼。如是把粱马骗到家里,只送文房四宝,不准送饭,想把他饿跑。黄妹子用杂粮烙成纸一样的薄饼,送给粱马,让粱马度过难关。后来,粱马考取状元,二人结为夫妻”等。另外,还有人们带着煎饼闯关东,以及与煎饼相关的许多故事。
煎饼的故事很多,但于我而言,煎饼那是一种常常徘徊在心灵深处的有关于母亲的记忆。那些记忆的画面虽然已经泛着微黄,但却更能让我感受到一种心灵触摸的情感体验。因而,表妹每次送煎饼来时,都勾起我的回忆。尤其是天放亮时,母亲在窗外推磨的那个身影!特别是母亲累的腿疼时,强忍住,不想让我看出来的那种让我再也忘不了的表情!
如今,馒头,米饭,以及各种花样的面食,已经成为普通百姓的主食,在餐桌上,煎饼已经少见了,即使见到的,也大多是机器煎饼。农村各家各户的磨盘,大多已被收集起来,化成了另外一种风景;用于烙煎饼的鏊子,也已难得一见了……尽管这样,尽管我们现在见到的煎饼大多是用机器做的,但煎饼却以其特有的乡土性、黏着性,以及深藏不露的韧性和它那种特有的形式,在人们的记忆和情感里深深地扎下根来。
一张张圆圆的看似不起眼的煎饼,也许正是面对我们的大本大原,它与太阳,与月亮,与空气,与山,与石头,与土地,与水,与一方土地生长着的庄稼,与一方土地上的人,与一方土地上所有的生生死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正因为这样,妹妹从临沂过来探望母亲时,母亲总会嘱咐我,让我别忘了给妹妹买包煎饼带着。是的,在一个村庄,在一个地方,甚或在一个广阔的区域,祖辈们为了生存下去,年复一年的,在一方土地上踏出一条有别于其它地域的生存之道。在这条道上,有着属于一方土地原生的具有本土特质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已经深入到人们的基因里,那里面深藏着一种舍弃不掉的情感记忆,它让人相信生命所生活的脉络中,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影响着那个生命,它因而一年挨着一年地延伸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尽头。因而,那煎饼始成为同一个地方的人们共同背负着的,从小到大到老一同生活过的有关于生命延续的珍贵记忆。这种记忆让每一个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都能真切感觉到自己生活的厚实和深远,甚或感觉到一种之于人的生命的那种无限的存在。
因而,那煎饼让母亲,让表妹,让我,让一方水土养育起来的那些说着一口乡音的人们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双脚深深地踏入这方土地!眼下,尽管时代在改变,工业文明在扩张,信息化在普及,但却很难让人从故乡的泥土中拨出脚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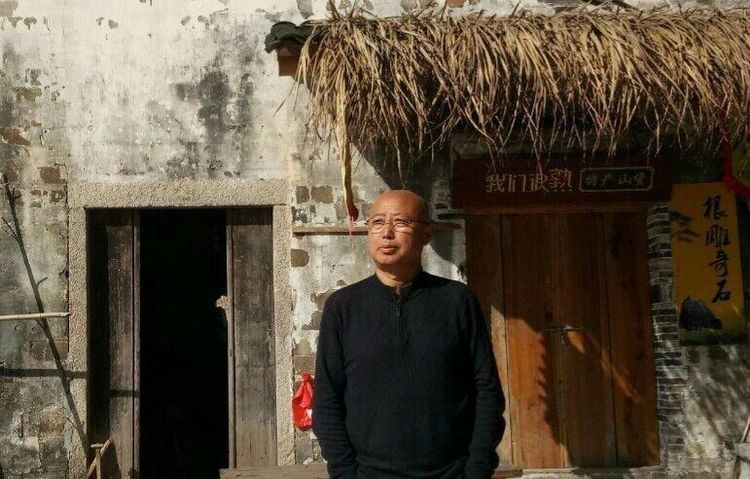
冯春明,沂南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有诗歌、散文、文学评论见于《山东文学》《山东作家》《前卫文学》《时代文学》《延河》《九州诗文》《青岛文学》等。著有散文集《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