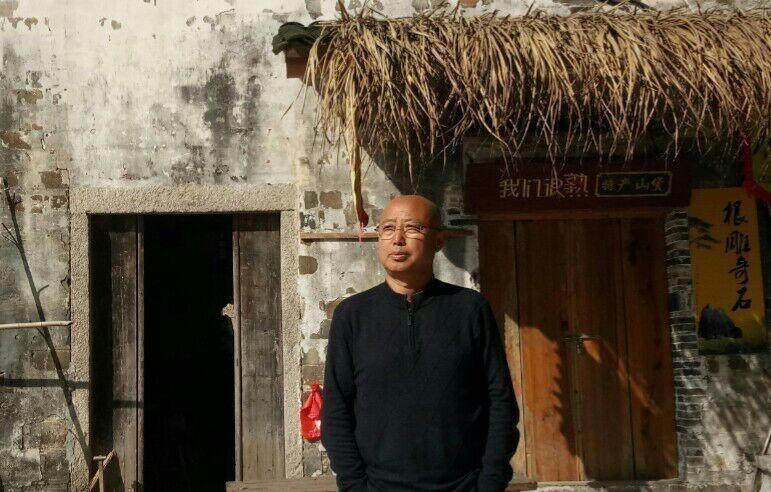在中国历史上,当楚汉之争这场大戏落幕之后,一直持续回旋在我脑海中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也慢慢地淡了下来。但是在这场大戏的边缘处,有一个人连同他身后的那一群人,却在我的眼前越发清晰了起来。那个人和那一群人就是在这场大戏落幕之时,应召赴洛阳都城途中拔剑自刎的齐国历史上最后一位齐王——田横,以及与田横同行遵从田横遗嘱完成任务后自刎的两个门客和从齐国一座小岛上赶来的在田横墓前自刎的五百名追随者。
古代中国有许多杀身成仁之士。但像田横他们这群人那样在一个人自杀后,后面紧接着又有两个人、数百个人,因为一个“仁”字一起先后而自杀的悲壮场面实属罕见!像这样惊世骇俗的事件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可能仅此一例。
当时,在这个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社会文化急剧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一幕,可以说,那是完全超出人们想象范围的。是的,眼前所发生的这一连串地以结束自身生命的方式而殉道的场景,是有史以来神州大地上最为壮烈的历史造型。它从本质上来讲,并不适于惯常的通则和规律,也有违人们之于生命价值的珍重。但是它出现了,它出现在一个过往的社会框架被拆解;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渐趋形成的过程中。它在历史的天空中,以一种极具个案特例的形式,一再让人们用十分吃惊的目光,对这一方土地的文化脉络重新加以了解。
人类毕竟是一个有感情,有价值理念,有内在追求的群体;这个群体除了在这个物质世界里追名逐利之外,仍有其肯定或否定的价值。田横和他的追随者们生存的这方土地,它“东滨大海,北临黄河”,淄水、济水、时水交汇其间;它“南望大野,西近雷夏,泽薮遍布”;它的都城临淄——位于古老东夷的轴心地带。在这方神奇的土地上,东夷这股以凤鸟为图腾的文化血脉源远流长。
公元前1045年,自周朝封赐出生于黄海之滨的姜太公为齐国君主后,至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一统天下;上下七百多年间,齐国作为一个诸侯国,一直有其文化上的独立性。周之前,齐地即有“衣冠带剑”、“仁而好生”之称。周时,姜子牙“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使齐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齐国虽几经历史变迁,但其文化却是一脉相承的。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期,位于齐国国都临淄稷门附近的稷下学宫与古希腊雅典学院并称为“轴心时代”。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曾三次来这里担任祭酒。稷下学宫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也是我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和政府智库。它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等诸家学派。其兴盛时期汇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稷下学宫的存在,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此期间,有《宋子》、《田子》、《蜗子》、《捷子》、《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等学术著作相继问世。
稷下学宫前后历经了一百五十余年。宣王时,受上大夫称号之稷下士多达七十六人。稷下学宫的这种“从了解到包容并欣赏其它文化”的立场,慢慢地形成了齐文化独有的特质。因而在齐文化中——以“礼法结合、义利并重”的这种互补式政治,形成了有别于先秦地域文化的“变革性、开放性、多元性、务实性和智慧性”的地域文化特色。
汉前,齐国虽然经历了秦始皇残暴的统治,但却未能撼动这方深入到人们骨髓的文化根基。秦末,随着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身为齐国贵族的田横与兄长田儋,在今山东高青县一带举事反秦,齐国文化也因而得以延续。
秦灭亡后,楚汉之争愈演愈烈,身处楚汉之外的齐国成为楚汉争相占领之地。项羽攻入齐地后,齐王田荣兵败被杀。期间,田横收集残兵,固守城阳。这个时候,被后来的清朝女作家李晚芳评价为“羽之神勇,千古无二”的项羽,亲帅大队人马,猛扑城阳。当时,田横手下只有一万多人,但是,项羽连攻数月,仍然相持不下。后来,项羽因其它战事牵扯,不得不撤兵。这是在当时各股实力中,以弱小的力量直接硬碰硬的面对凶悍的西楚霸王时,一个前所未有的战局。
之后,刘邦派郦食其做说客,劝“齐归汉”。时任丞相的田横接受郦食其的意见,解除了历下的防备。然而,韩信却听信蒯彻谗言,发兵突然袭击,一举攻入临淄。田横见汉军背信弃义,一怒之下烹杀郦食其。而后,齐王田广东逃高密,项羽派龙且带领军队救齐……韩信大破齐楚联军,杀死楚将龙且,俘虏齐王田广。田横随自立为齐王,转过来与灌婴交战。
刘邦称帝后,田横带领部下逃往黄海中的一个小岛。刘邦听闻,随派使者赦免田横,召他入朝做官。田横因曾烹杀郦食其,郦弟又是朝中将领,不敢奉诏。刘邦又再次下诏,保证不伤害田横,并说:“田横若来京,最大可以封为王,最小也可以封为侯;若是不来的话,将派军队加以诛灭。”于是,田横和两门客乘驿站马车前往洛阳。
路上,行至河南尸乡驿站时,田横停住脚步。他对汉使说:“作为人臣拜见天子应该沐浴一新。”于是在驿站住了下来。在驿站,田横对他的门客说:“我田横和汉王都曾是称孤的王,现在汉王做了天子,我却成亡国奴,还要称臣于他,这是莫大的耻辱。更何况我杀了郦食其,再与他的弟弟同朝并肩,纵然他不敢动我,难道我于心就毫不羞愧吗?再有,皇帝召我来京,不过是想见我一面。现在我割下我的头颅,你们快马送去,我的容貌不会改变,就让皇帝看一下我的样子罢。”之后,田横面向临淄故土,口唱:“大义载天,守信覆地,人生贵适志耳”……随即横刀自刎。随后,两门客手捧田横头颅,跟随使者飞驰入朝,奏知刘邦。刘邦看到田横头颅后,流下了眼泪。他封两个门客为都尉,并派两千名士卒,以诸侯王的规格安葬了田横。
安葬田横后,两门客在田横墓旁拔剑自刎。刘邦闻讯,为之震惊,又派使者召岛上五百人进京。遂发生了五百人集体自杀的一幕。这一令人震惊的画面,让我想起《礼记·儒行》中:“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这句话来。继而我又想,它或源于辜鸿铭所认为的中国古人那种“深刻、广阔与单纯”的性情,以及那种人之秉性的纯粹,而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是的,从他们那些让人看起来“不太为冰冷的理智所左右,而有很浓厚的人情味”的言行来看,这群人所带给人们的更多的是一种古朴实在之感!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他们才“具有一副成人的头脑”,又具有“一颗赤子之心”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的。我想,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他们的归去或许正是一个古老国度的归去。他们的造型恰是我借以解读齐国时,所窥见的那个古老国度的缩影。
本文写到这个地方时,我不由得面向那群远去的背影,默默地起身致敬……齐国历史的过往虽然没有给我一个整体上的视野图像,但是,每当我回看这幕影像时,每每对以凤鸟为图腾的东夷民族生发出许多感慨来。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田横没有选择那种被一再重复着的“合作”,而是不再向前多跨一步。这种率真、平实的姿态;这种人性化的表达;这种固有的贞节观念;这种视死如归的壮烈;以及他与他的追随者们的这种义无反顾的选择,让我想起了古希腊酒神祭中那种“粉碎了”而后“死而复活”的场景……当然,他们的选择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许是不可思议的,但却又是真实的。今天的我们无论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它,无疑,它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上已经留下了颜色最为浓重的一笔。这一笔留痕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胎记。
人世间没有什么比在世俗的洪流中不被玷污,不被扼杀,并保持住自己灵魂的洁净,保持住良知中的人性,更加困难和更成问题的了。但是,在历史的尘烟中,田横和他的追随者们做到了。有关于田横他们的作为,无论今天的我们作何理解,那都是这方土地上生发出的一束极具本土性的生命光辉!那都是一道道源于这方土地的“神圣根源”的灵光!
今天的人们在田横驻足的地方又向前走了2200多年。此刻,当我面对街市上那些匆匆忙忙的身影时,我想,我们是否如印第安人那句谚语所言:“身体走太快,要坐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