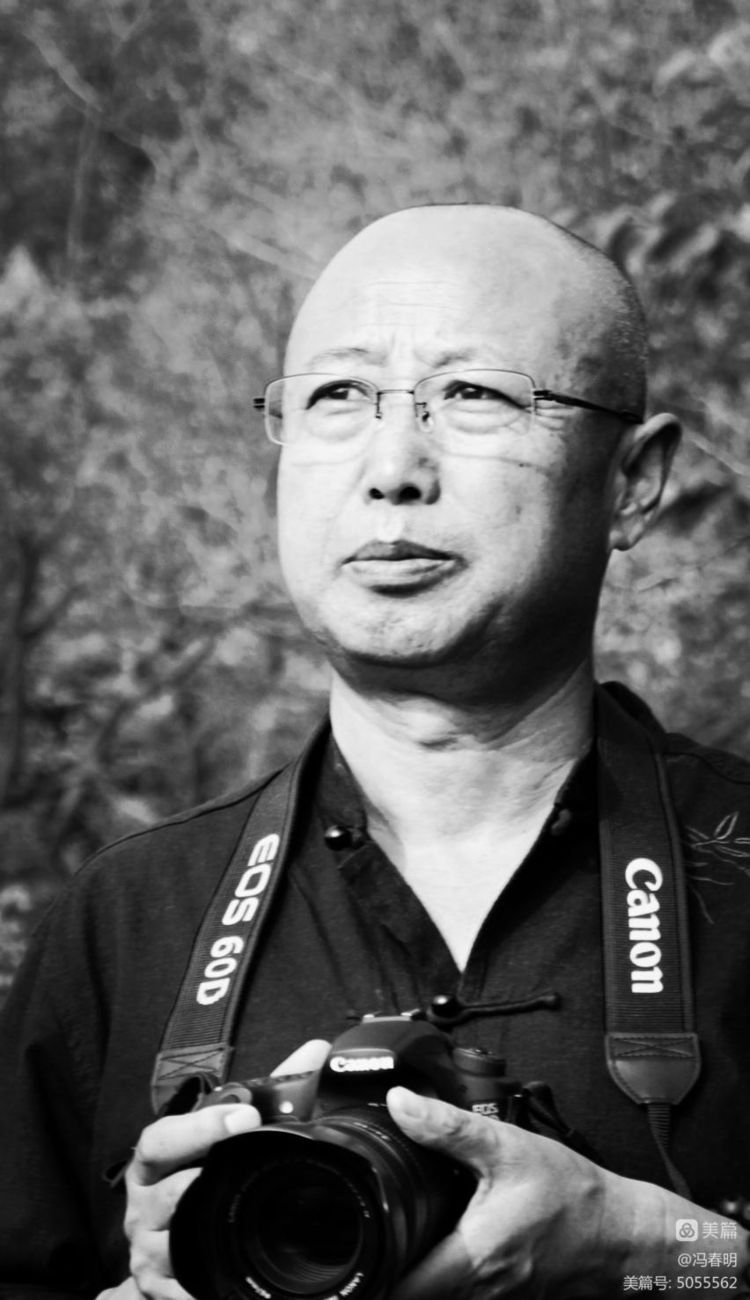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莒县陵阳河上空突然电闪雷鸣。不一会,陵阳河水开始上涨,河床两岸的泥沙开始一层一层地脱落,一个造型古怪的陶器慢慢地从黄泥中露了出来。这个时候,整个陵阳河上空持续地电闪雷鸣,河床上,随着河水不断地上涨、不断地撞击与冲刷,那个陶器的表面,有一个朱红色的神秘符号,让在场的人睁大了眼睛。这个造型古怪陶器上神秘的符号,让闻讯赶来的考古专家激动不已。专家认为,这个陶器上的神秘符号有可能改写中国文字发展史。
这个造型古怪的陶器被称为“陶制大口尊”。后来,陵阳河又相继出土了多件陶制大口尊和大量的陶制牛角号、陶制酿酒酒器、陶制饮酒器具等。早在新石器时代,在莒县这片土地上就形成了以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为中心的古代文化区。莒县历史悠久,商代为姑幕国,春秋时为莒国,汉代为城阳国。在这片土地上有古城堡遗址10多处,古遗址、古墓葬1291处。仅莒县博物馆就收藏了12000余件出土文物,其中,国家级文物200余件。
莒县属于古代东夷的范围,是“海上日出,曙光先照”的地方 。考古学家曾在东夷这块土地上找到了40万年前的人类头盖骨。数千年前,这里的原始先民,他们在大海边,在山上、山下,在大野、河流,年复一年地捕鱼、狩猎、农耕劳作。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东夷人靠着他们聪颖智慧的大脑和勤劳灵巧的双手,制造出实用精美的石器、骨器、玉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烧出了陶罐、陶鼎、陶制大口尊和薄如纸、黑如漆、面如镜的蛋壳陶;编织出布纹细、密度高的麻、丝纺织品;发明了冶铜术、原始历法和最古老的文字,兴起了种植业、家禽饲养业和酿酒业。
位于莒县城中的莒县博物馆展厅,有一种来自远古、悠远深沉的古老文化气息充斥、弥漫在各个角落。透过久远的年代,那些充满神秘意味的各种石斧、石铲、陶罐、铜鼎、铜罍……以一种深沉而生动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眼前。它们似乎是为了与人们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而来的。这些石制的、骨制的、陶制的、玉制的、铜制的,有着各种形状的器具,浑身散发着一缕缕尚未摆脱原始意味的微光。它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款式,以古朴凝重的姿态和造型,以流畅、简洁的纹饰和色彩,处处流露出敦厚、沉静,又不乏深邃、神秘,拙朴、奇异的意味或心绪。
去莒县陵阳河一直是我的一个愿望。这个距离我读书的沂南县郭家哨联中仅有22公里的地方,却间隔了我半个世纪。50年前的那个初秋,我和联中行将毕业的同学们一起翻过浮来山,去了十几公里外的莒县城区照相馆拍毕业照。那是时间最早,距离莒县陵阳河最近的一次。后来,虽然又有许多次接近陵阳河,但却屡次与陵阳河擦肩而过。因而我想,今天来陵阳河大概是一个定数了。
今天,正值酷暑。停下车,打开车门后,空气烫人。陵阳河中心广场前,博物馆大门紧锁。我问正在馆前树荫下排队做核酸检测的一个中年人:“陵阳河出土大口尊的地方在哪里?”他告诉我,广场东边向北,那个大门楼下的河沟就是。
陵阳河已被改造取直。两边用石头垒砌的河堤,让人很难看清河流曾经的面貌。站在陵阳河边向东望去,可隐约看见一座不高不矮的山。我联想到陵阳河出土陶制大口尊上那个“日月山”图案,于是驾车向那座山奔去。
这种直奔目标的方式,让我的汽车吃了不少苦头。那条本来就窄的土路,被大雨冲刷后,路上的石头、坑洼全部露了出来。那些尖锐锋利的石头,让汽车无法躲避。上坡时,车轮一次次发出让人心疼的碰撞摩擦声。还好,我的汽车总算是越过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自己并不孤单,自始至终有一股力量伴我前行。
不一会儿功夫,坡的上方有一条南北向的公路出现在我的眼前。道路虽然不宽,但跟我刚才走过的道路相比较已经够好的了。我右转车头,沿着公路向南,在不远处一个卖瓜的敞棚前停下。在这里,可以近看东边那座山。
盛夏,植被茂密,东边那座山的山体被各种树木遮掩,很难看清它本来的面目。卖瓜的中年妇女告诉我说,这座山名叫四姑山(寺崮山)。传说,有四个尼姑曾经住在这座山上。夏天发大水时,下面的河水会向山上倒流,所以淹不了村庄。我问她家住哪里,她说,她家就在北边不远处的东上庄。东上庄那条河就是从寺崮山上流下来的,村里人叫它大雁河。这条河由东向西流淌,很快进入陵阳河,流入接水河,汇入沭河。
大雁河水流清澈,站在公路桥上,可以目送大雁河水进入陵阳河,进而可以看见,这股水脉与陵阳河一起注入了一片开阔、肥沃的平原。站在这里似乎可以做出结论:眼前这片被诸多村庄和小镇占有了的土地,曾经是一片雨水丰沛,涓滴成河的地方。古代任何一个部落,只要踏足这里,都能安心度日,繁衍生息。
我因公元1960年夏天,经过一场暴雨冲刷后,从陵阳河露出神秘面纱的陶制大口尊而来。多年以来,有许多专家陆续发表了他们的观点。有说陵阳河出土陶制大口尊“日月山”图案是太阳、月亮、山脉的组合;有说“日月山”图案上面的圆型代表太阳,中间部分为云气,下面是山峰。更有学者认为:莒县陵阳河出土陶制大口尊和随后出土的众多陶器上那些各种各样的符号,是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而且,他们还对每一个“文字符号”进行了解读。
陵阳河出土陶制大口尊上这个神奇的图案,越是众说纷纭,越让人感觉到一种莫大的诱惑力。它就像是一首神秘而朦胧的诗,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领略通体之美。这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学说,各有各的道理。陵阳河出土陶制大口尊距今五千多年,它让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域的古老文化露出了神秘一角。自此之后,有许多人围绕着陶制大口尊上这个神秘的符号,围绕着这方神秘的土地,反反复复地做了许多深入的考究。有人甚至从寺崮山的影像中,找到了让他们激动不已的吻合点。他们利用在寺崮山日出时拍摄的影像和人工标出的图案进行重合比对,找到了二者十分相似的结合点。从这个影像标记符号中可以看出,影像制作者倾向于把陶制大口尊“日月山”图案中间的符号看成是云彩。的确,影像中——当太阳从寺崮山后冉冉升起的时候,天空中泛着七色霞光的云彩,以及云彩下面的山头,与人工所画图标神秘的对应在一起。此情此景,十分令人称奇。
陶制大口尊生成的时期,处在与良渚文化同期的大汶口文化中期,甚或更早。过往,考古学家把大汶口早期文化称为“东夷文化”或“海岱文化”。莒县陵阳河处在这一文化区靠近黄海海岸的地带。这一地域距离黄海海岸线不足70公里,它面朝大海,土地肥沃。从陵阳河出土的陶制大口尊和陆续出土的众多陶器上,那些被专家称为中国最为古老文字雏形的各种符号和薄如蛋壳的黑陶,它们并非人类一时兴起的创造物,它的文明创造之长度,甚至比自殷墟甲骨文出现后,这段开始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更为漫长。甚或可以说,人类有文字记载之前,那个漫长的史前文明期,更是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梦一样的存在。
古人曾有“伏羲画卦”之说。作为东夷首领的伏羲,他的“画卦”“飞鸟说”大概源自于上古时期的鸟图腾崇拜。这点与东夷民族的鸟图腾崇拜是相互吻合的。可见那个时候,古人的抽象概括能力已经够强得了。陵阳河陶制大口尊“日月山”图案,或许与这一地域民族最初的图腾崇拜有关。在这片面向大海,最先迎接第一缕阳光的土地上,太阳、大海、土地,才是人们生命印象中最为深刻的部分。
图腾崇拜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原始信仰,图腾源于生活中的具体形象,及其抽象的想象或者图案,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专家学者把陵阳河出土陶制大口尊图案中,最上方那个圆看成太阳是没有疑问的,它应该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陶制大口尊中间那个看似月牙状的符号,它的弯处有一个向上凸起的尖,类似于鸟的嘴,那鸟整体上处于展翅飞翔的状态,很像海燕或海鸥的形状。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陶制大口尊“日月山”图案中间这个符号——海燕或海鸥,它所表达的内容就有寓意大海或面朝大海的意思了。
为了验证这种判断的可能性,我在网络上搜集了海燕、海鸥飞翔时的照片,并用它们与陶制大口尊“日月山”图案中间的那个图形进行比较,发现它们之间具有相似性,这让我进一步相信自己的判断。而在东夷民族“以鸟为图腾,以鸟名为姓氏,以太阳为神祗”的记载中,“鸟和太阳”与陵阳河出土陶制大口尊图案中的元素构成相互吻合。包括后来掌握了商朝王权的东夷分支、商之始祖契,传说是一个名叫简狄的女人,吞服“玄鸟卵”怀孕而生。亦即《诗经·商颂》所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些传说和记载,都与鸟图腾崇拜有关。
当我们沿着商王朝的来路,逆向寻找它的源头时,很容易与陵阳河出土陶制大口尊图案中那只“鸟”的原型联系在一起。包括商人把水滨的鹬鸟奉为风雨之神,大旱之时,将鹬羽戴在头上,模仿鹬鸟祈雨。以及古人利用刻有鸟和太阳图案的陶制大口尊盛装美酒等,这些或许都与东夷这个古老民族的鸟图腾崇拜有关。本着这个思路,我们能否把陶制大口尊上的图案看作是一个与祈雨有关的符号或文字呢?相关历史文献中有“商人焚祭”,“癸巳贞,其燎十山雨”的记载。意思是说,大旱时候,商人时常用焚山的方法进行祈雨。在东夷神话传说中,上古时代就已经有了司雨之神。本着这个线索,把陶制大口尊图案最下方那座像似正在燃烧的山,与商人焚山祈雨的习俗进行联系、比较和思考,我们会从中发现某些史前时期祈雨文化的史影。总之,无论是把陶制大口尊上的“日月山”图案作为东夷民族的图腾去理解,还是作为东夷地域的象征——“太阳、海鸟(大海)、山脉”去理解,或者把它作为与祈雨相关的符号或文字去理解,它们与面向大海、最先迎接第一缕阳光,以鸟为图腾的东夷民族,都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为了寻找到陵阳河出土陶制大口尊的准确地点,我又从寺崮山折回,在莒县陵阳镇一个名叫河北小寺村的地方,找到了一块山东省1992年公布的“陵阳河遗址”立碑。石碑在陵阳河北岸,石碑东是一条贯穿村庄南北的大路。大路由一座不大的石桥连接两岸。路东有两位80多岁高龄的老妈妈,我向她们打听陶制大口尊出土的情况时,她们不知情。我又到对面一家磨面房询问情况。磨面房老板说,凌阳河水过去很浅,下雨后还有人能拾到盆盆罐罐,那些盆盆罐罐都是从黄泥里面冲刷出来的。现在河水加深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
站在这里的我如同站在历史的高处,四周苍茫而辽阔。眼前,陵阳河,这条看起来不大的河流,处处弥漫着神秘的光影。从这里出土,被黄泥包裹,刻有神秘符号的陶制大口尊,内里充满了智慧、梦想和渴望,那是古人通过火光显灵于泥土的一种存在。它的出现,认证了身处遥远时空中的东夷人,在这方土地上所进行的,那场极其漫长的精神性成长。
世事变迁,物是人非。我驻足河岸,冥思良久。其间,西北天空乌云翻卷,雷声阵阵。那雷声如同鼓点,越来越响,整整持续了一个时辰,但却没有下雨。此刻,在我的视野里,天地大时空与史前大时间交织成一种别样的视界,它让有点懵懵懂懂的我,于大脑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亚麻色的精灵,它忽明忽暗,飘忽而来,那精灵犹如穿越时空的使者,让我的思路沿着雷声对应的方向翻过寺崮山,向着汹涌的大海飞去。继而,那雷声与大海的波涛声遥相呼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