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子”冯桂金在南昌八一纪念馆留影。)
E711 冯春明:“ 一家子”——记沂南书痴冯桂金
一家子

冯春明
2021-09-25
阅读 1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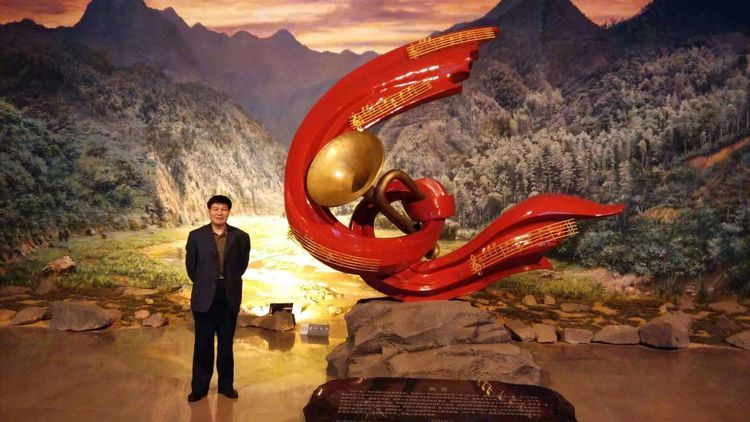
记得那是2003年春节后的一个下午,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对方称我“一家子”的电话。一问,原来是在沂南县国税局办公室工作的冯桂金。桂金说:“我收藏了点东西,你有空的话来看一下。”听说“一家子”有藏品,我立马答应了。
下班后,我按冯桂金告诉我的住址,开车直奔国税局家属院。但见“一家子”早在楼下等我了。
三楼,一个不到100平米的居室,各种藏书占去近半的空间。天!这是家?还是藏书馆?我迫不及待地走到藏书架旁。冯桂金笑着跟我说:“‘一家子’先别急着看,咱们喝两盅再说。”这时,女主人把早就准备好的四个小菜和一瓶高度酒摆在客厅茶几上。我们两个便推杯换盏了起来。酒近半酣,我才如腾云驾雾般地游历于这文山书海之中。
从客厅到书房,从书房到卧室,从卧室再到隔壁藏室……整个的,一个家的四周全是书!那是一本本古香古色的线装古籍,它们有序的静静地排列在书架上。这里:书札、精抄,金石类、文史集类、史志类,谱牒类、术数类,韵典律类、宗教类,小说戏曲类,医药类,四书五经类、科试类,它们一队队的各成体系。这成千上万的古籍,让我有眼花缭乱之感。此刻,本想浏览一下的我,竟无处下手,且略显慌乱。这些精灵,这些如同远航归来的水手般的精灵们,它们睡着了……它们已经很累,静静的“港湾”里,那睡姿让你真的不忍心再惊醒它们。
“一家子,这些书是我多年来,利用闲暇时间,下乡跑古玩店收购的。”冯桂金说。“一家子”的话让我心头一颤。哦,是这样的!这一个个散失在各个角落的孤独者,他们在“一家子”的寻找下,终于到家了。茫茫人海中,是“一家子”辛辛苦苦地找到了它们,并让它们找到了散失在各地的“亲人”,且一起团聚了!
此后,这书、这人,它们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在想,几千年来,这众多的古籍,历经战乱,历经朝代地更替,它们几经失散,四处奔波……如今,是该让它们休息一会儿了。它们需要回家,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冯桂金——这位四处奔走,嗜书如命的收藏家,不正是他们的接站人吗?此刻,我仿佛看见,在车站、在码头,在路上……一位风尘仆仆的中年男子,正在喧嚣的行人间徘徊、张望,他在期待着一个个身心疲惫的“游子”出现,他要领他们回家。
此刻,望着虔诚地行走在藏书路上的冯桂金,我突然领悟了“一家子”的深刻含义。
翻开冯桂金所著《阳都冯氏藏线装古籍图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书札》(一)。这些散发着生命温度的书信,今天读来,依然让人倍感温馨。《书札》是人类传递信息的一种载体,一般由主人亲笔书写。“客从远方来,遗我书一札”……古诗《客从远方来》中那些饱蘸情感墨迹的诗句,每每读来时,让人动容。
《书札》(一)中介绍的,是由清末书画家徐寿昌,叙州知府史崧秀等八人书写的“楷书洒金绢清写本”,它们字字如矶,鲜活如初。每当将其捧于掌中之时,即感馨香四射,余音袅袅。
在史志类中,由陈邦瞻纂辑,明万历版《通鉴纪事本末宋编》,是一部完整的竹纸线装书,这是冯桂金的珍藏品。陈邦瞻字德远,江西高安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曾任南京吏部稽勋司郎中,后官至兵部左侍郎,《明史》卷二四二有传。在他之前,“一家子”冯琦和沈越都用纪事本末体编写过宋代史事。后来,他们的弟子请陈邦瞻将二人之书加以增订。陈邦瞻将二书合为一编,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着手编撰,历时约一年完成。
线装,木刻版本,是冯桂金藏书中的重要部分,它占冯桂金藏书量的70%。雕版印刷技术在中国最早开始。唐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868】年)刻的《金刚经》卷子,是全世界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印本书。北宋雕版印刷进入兴盛时期,活字印刷呼之欲出,应运而生。此后,出现了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共进的格局。但是,由于活字印刷技术的局限性,直至明末清初,雕版印刷仍处于主导地位。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典籍也不例外。于是,从古至今,有这样一个群体——私人藏书家队伍,他们嗜书如命,倾其毕生精力构筑古书典籍的家园。他们代代相承、源远流长,将中国浩瀚的古代典籍世世代代保留传播了下来。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经济收入极其有限的工薪族人,他从商人那儿毫不吝啬地收购着古籍。有次,他和一位藏友骑摩托车到一家古玩商人那里收书回来的路上,不幸与一辆对面驶来的摩托车相撞,眼部被反光镜切开了4厘米长的口子。导致颅骨骨折,脑部出血,在医院住院达一个半月。那次创伤在他的眼部留下永久的疤痕,但他依然驾驶着他的摩托车,穿街走巷。他“没有停止藏书的步伐,相反,藏书的决心更加坚定,信心更加充足,步子更加坚实,收获更加丰厚。”因为,痛苦是暂时的,很快,他就被收获的喜悦冲刷得一干二净了。他就是“一家子”。
我跟冯桂金说:“‘一家子’你足可以称为藏书家了。”冯桂金没有回答,只是莞尔一笑。所谓“藏书家”,据《中国私家藏书史》所引,《四库全书》乾隆的“圣谕”标准是:“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当然,这只是指藏书数量上的多少而已。清朝的“百种”到了后来,大概就以“万册”来代替了。冯桂金的藏书何止百种万册,但他从来没把自己标榜为“藏书家”。他在博客笔记上说,自己藏书的数量有限,再加上眼界、地域和经济能力的限制,已经决定了自己藏书面窄、质量差、数量少。收获的也是有限的。经过长期的积累,也只是聚集了这千多套散落在乡下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古书。好一个“散落于乡下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古书。”恰恰就是这些存在于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的古籍,是最容易失散和最为珍贵的。冯桂金的作为无疑是对历史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他从而让我感受到那种淡泊名利的品格和对历史文化的强烈责任感。
如今,冯桂金仍然在他的收藏路上艰难跋涉着。他在他的收藏之路上写出了150万字的《中国近代税票研究》(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又以鲜为人知的详实资料,写出了600万字的《中华民国地方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约定出版),同时,又开始了词牌研究……沿着他的足迹,我深切感受到了一种极具人文意蕴的重量和声音!人生的道路上,我发现他和他的藏书已经融为一体,“藏书”已成为他灵魂的支柱,继而化作他生命的本身。
冯桂金算不算藏书家,我没有资格妄加评判。我只知道,我不能随便打扰他。近些年来,正在潜心研究藏书的“一家子”,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他除了用于作息和锻炼身体的时间之外,每天工作到凌晨一点。他的成就虽少为人知晓,但我从他的家,从他的藏书;从他“静守书斋,破读典籍”的身影;从他归纳成集的《阳都冯氏藏线装古书图解》,以及他的一系列著作中,真切地发现,他的确是“一家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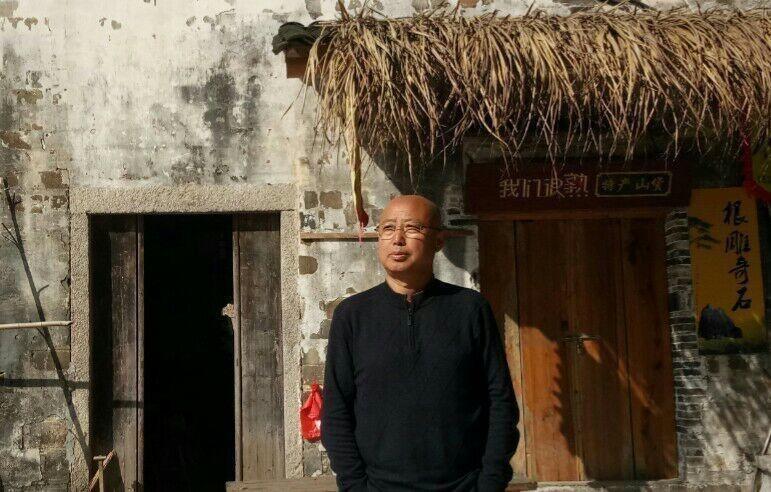
冯春明,沂南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有诗歌、散文、文学评论见于《山东文学》《山东作家》《前卫文学》《时代文学》《青岛文学》《延河》《九州诗文》《星星》《诗刊》等。著有散文集《如是》。
更新于 2021-0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