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08.冯子栋: 只留清气满乾坤(随笔)
父亲已去世两年了,一直想写写他,却总担心自己笨拙的笔难以写好。犹豫再三,终于鼓起勇气提笔一试。

(一)
小时候,我和弟弟喜欢跟着爷爷去上坟.
路上人来人往,有老人也有孩子,热闹。我们抢着帮爷爷挎提篮,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一溜烟儿地小跑,颠得碟儿碗儿叮叮当当地响。那时的供养菜很简单:一片金黄色的薄薄的鸡蛋皮,一块方方正正的豆腐,一块腌存已久的方肉。别看菜品简单,那可算是咱老百姓家里最好的菜啦。尤其那块方肉,真可谓压箱货啊,用盐粒子培起来,一家人平时不舍得吃,能存放大半年,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才端上桌撑撑面子。
我们虽然有模有样地学爷爷磕头,但是从没见过茔坟里那些老人生前的模样,所以并没有伤心的感觉。
上完坟回家,正是太阳傍山的时候,跟在瘦瘦长长的影子后面,肚子咕噜咕噜直叫,瞅着碗里那落了一片片纸灰的饺子,直咽口水。爷爷疼我们,让我们边走边下手抓着吃,一口一个,还没到家就吃完啦。
后来,爷爷老了,上坟的事由父亲和叔叔办理。
父亲对上坟这事非常重视。他提前好几天买来香蕉、苹果、葡萄。这天,母亲炒几样小菜,包好饺子,他拿出一瓶酒,沏上一壶茶,打好一摞纸,把供品分别放在提盒、箢子里,挑着挑子去上坟。
老少爷们外出打工的多了,上坟路上已没儿时那么热闹了。父亲那挑着挑子的身影,显得突兀、古板。
从上香、摆菜、斟酒,到燃纸、奠酒、叩拜,父亲都一丝不苟,恭敬虔诚。他不仅给自己的老祖上坟,还受外地宗亲的委托给他们的老祖上,一圈下来得整整一个下午。
我考学出来后,回老家上坟的次数少了,只是偶尔陪父亲去一趟。其实,内心并不乐意跟他一起,每次看见他那迂磨、认真的样子,我就抱怨:人家上坟都是简简单单的一刀纸、一炷香、一样菜,为何到了咱这儿就搞得这么复杂呢?老人在世时好好孝敬他们,人没了,象征性地纪念一下不就行了吗?
面对我的抱怨,父亲总是连连摆手,撂下一句“你不懂”就再也不理我了。
谁说我不懂?我一肚子不服气。
(二)
我们家是一公一农的家庭,父亲在农行工作,母亲在老家务农。
父亲退休后,一门心思地研究起族史来,一到农闲就外出寻访。我和弟弟并不赞成他做这事,觉得这是个耗时间耗精力耗财力的活儿,再说跟咱平常过日子也不沾边。我们盼着他和母亲一起来城里住,帮我们照应一下孩子。可他认准的事啊,八头牛也拉不回来。
母亲虽然不识字,虽然常因生活的琐屑跟父亲发生争执,但在这件事上却一直支持父亲,说他这是为老少爷们做好事。
每次回老家,总看到父亲的床头案边堆着一摞摞族谱、碑文的复印件,还有他写的那些密密麻麻的笔记。他兴高采烈地讲他去费县、沂水、沂源、临朐、青州等地寻访的所见所闻,讲家族繁衍迁播的来龙去脉。那时,年轻气盛的我对那些事压根就不感兴趣,听不进去。
二零一三年,父亲来我家住了一宿,用黑皮绳背着个尼龙篮子,篮子里装满了族谱资料,说要去江苏邳州祭祖,说那儿有六百年前老祖宗的茔坟。我在心里嘀咕,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在意那六百年前的老祖宗呢。
那时,邳州宗亲正倡议修族谱、建祠堂。父亲回来后积极宣传、动员老少爷们。大家都拍手叫好,可真正能帮上忙的并不多。比起过去,人们现在的家族情感已经淡漠了许多,各顾各的,以血脉基因维系起来的家族向心力也已经散了。
执拗的父亲,在无奈中前行。
二零一四年,我买房子,他没钱帮我,却悄悄为祠堂捐了一万块钱。
岁月如水,波澜不惊。
二零一五年,母亲在城里帮我看孩子,每逢周末就回老家收拾收拾。有一次,她意外发现父亲如厕时流了很多血,觉得不对劲,催弟弟赶紧陪他去医院看看。
检查结果,晚期直肠癌!
弟弟的来电,如平地惊雷,令我愕然惊惶。父亲的身体一直很硬朗啊,咋一转眼就到了癌症晚期呢?我失声痛哭,有生以来最悲恸、最难忘的一次痛哭。那一刻,左耳鼓膜穿孔。
我和弟弟拿着更改了的报告单匆匆赶回家,小心翼翼且故作轻松地劝他去医院把那个“息肉”切去。出乎意料的是,平时连感冒都哼哼歪歪的他却变得满不在乎:“是老毛病——痔疮犯了,不用手术,只要注意饮食就会慢慢好起来的。”
我们说服不了他。
他开始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用的碗、筷子、杯子单独放起来,还用石棉瓦在院墙外为自己搭了个简易的厕所。每隔几天,就独自把厕所里的脏东西提到屋后山冈的旮旯里,悄悄地焚烧掩埋。
原来他心如明镜啊。
我怀着敬畏之心重新审视他。
那个朗润、刚正、锋锐的他不知从何时起变得苍老、瘦弱、温言善语,脖颈后那个已长了多年的瘿更显得鼓鼓囊囊。我和弟弟靠近他静静地坐下,就像回到了儿时橘黄色的油灯下围桌而坐听他拉呱的情景。令我们吃惊的是,他不仅能把久远悠长的族史娓娓道来,而且对散落各地的五千多位宗亲的名字都了然于心。我这才知道,他在那十年的寻访中吃了很多苦头。他的那辆破嘉陵摩托曾好几次抛锚于荒山野岭;他骑着自行车曾被大货车别到沟渠之中,摔得鼻青脸肿;他曾赶了一上午的路才找到一家宗亲,人家却连口水也不舍得管;他曾提着礼品去人家求阅老族谱,人家却躲着不让看;登门征名,人家不在,好不容易找到了,名字却说不准,问多了,人家还有点烦;更有甚者,有人曾劈头盖脸地质问他,你是不是闲得没事干啦,搞这玩意儿能挣钱能当饭吃吗?
母亲悄悄告诉我,因为续谱,他还曾遭到我一个族兄的辱骂与殴打。
可怜的父亲啊!
我取过他床头案边的那些族史资料和考证笔记,仔细阅读。他的笔记写得特别翔实,但稍有点散。我跟他商量,想把笔记整理成一篇简要的文章。他同意了,并特意嘱咐我,一定要把那些曾热心支持续谱的宗亲写进去,要不然良心上会对不住他们。他侧蜷在床上,仿佛忘记了钻心的病痛,出神地盯着草稿,逐字逐句地与我讨论、斟酌。那场景,那神情,我终生难忘。
陪伴,虽然不能减轻父亲的病痛,却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莫大欣慰。一家四口坐在一起,仿佛回到了年少时的情景,屋外的小狗偶尔懒懒地汪几声,窗台上咔嚓咔嚓的闹钟声清晰可闻。那场不幸的遭遇,让我们的心紧紧靠在一起,让家变得无比温馨与和谐。曾经强嘴顶牛的父子,消除了彼此情感的隔阂,生出一种心灵相通的默契。渐渐的,他像孩子般依恋着我和弟弟。早上我们刚刚走出家门,他就来电话嘱咐我们回单位要好好工作,甭挂劝他。可刚一过晌,又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一些外地宗亲来看望他,紧紧握着他的手,一个劲地称赞他为家族做了一件他们想做却又无能为力去做的大好事。
亲朋好友隔三差五地来聊聊天,或静静地坐一会儿。大家用亲情友爱围起了一盆温暖的炉火。
二零一六年腊月二十七,他安然地走了。
我心中的天塌了,空落落的。
(三)
二零一七年清明节前的一个周末,天空晴朗。有十多位宗亲从二百公里外的邳州、兰陵赶来,专程祭奠父亲。在焚香叩拜的那一刻,一朵云悄然飘来,落下了几滴雨。我暗暗吃惊,是巧合,还是大自然隐秘的神奇?
母亲腰板不好,却执意要种父亲茔坟所在的那块责任田,她不愿让父亲看着那块地荒了。
今年春天,那块地因天旱而迟迟种不上花生,族侄冯英富叫上冯德友、公方富两位老人,瞒着母亲,偷偷帮我们浇地、翻土。母亲知道后告诉了我,我赶紧给他们打电话道谢,他们都说,谢啥啊,这点小事说不着。
七月十五中元节,传说这一天,逝去的灵魂会回到世间来看看。母亲特意包了父亲最爱吃的羊肉水饺,准备了他最爱吃的香蕉,炸了他最爱吃的萝卜丸子,拿出他最爱喝的银麦纯生啤酒,炒了几样小菜。
我拿出那个木质提盒。
突然觉得,上坟是一种神圣、庄重而又亲切的精神传承。
田间地头的荒草正肆意地疯长,地瓜地里的秧叶犹如墨绿色的湖水漫过层层地坝;玉米地里秸林高挑,森然幽深。绿色的屏障里,时常有蛇虫出没。当我和弟弟转到田间小路时,惊呆了:路边的杂草已不知被谁清理得干干净净,敞亮明净的小路一直伸展到父亲茔份所在的那块责任田。看得出,这是有人为了方便我们进出林地而特意清理的。是谁清理的呢?不得而知。刹那间,一股温暖的感动如电流般触通全身。
走近父亲的茔坟,供石台下竟板板正正叠放着好几刀崭新的烧纸。没想到,没想到,万万没想到。这又是谁放的呢?仍然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那是父亲的好友们让我们捎给父亲的一份份缅怀和念想。
我和弟弟趴在父亲的坟前,已热泪盈眶。
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如老家的那座山,低调谦和;又如冬日里的朵朵梅花,历寒弥香。
他们,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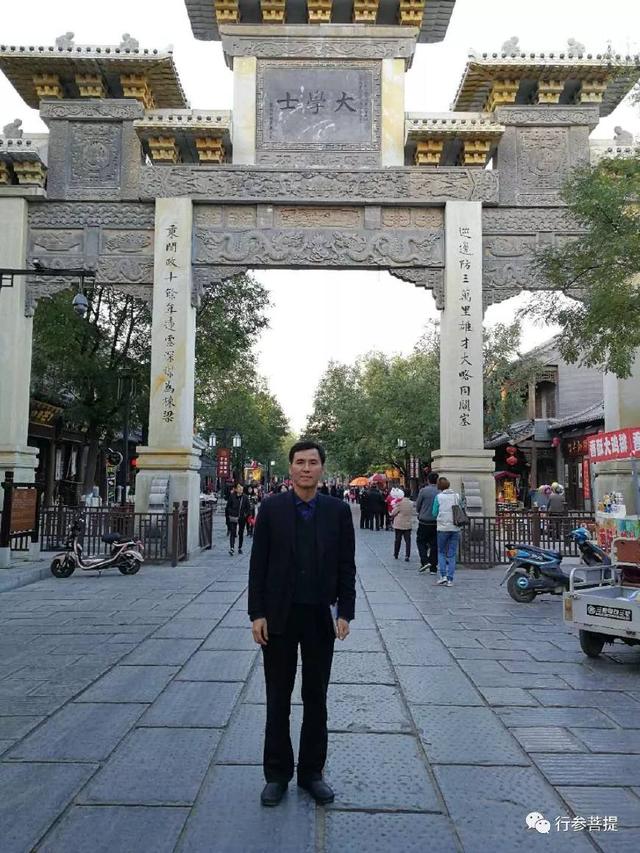 冯子栋,山东蒙阴人,现在临沂市农商银行工作。中国著名行走散文作家联盟成员,新媒体《行参菩提》签约作家。通过阅读来濯磨自身灵魂,通过文字来记录草根生活,通过经历来格物平凡人生。
冯子栋,山东蒙阴人,现在临沂市农商银行工作。中国著名行走散文作家联盟成员,新媒体《行参菩提》签约作家。通过阅读来濯磨自身灵魂,通过文字来记录草根生活,通过经历来格物平凡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