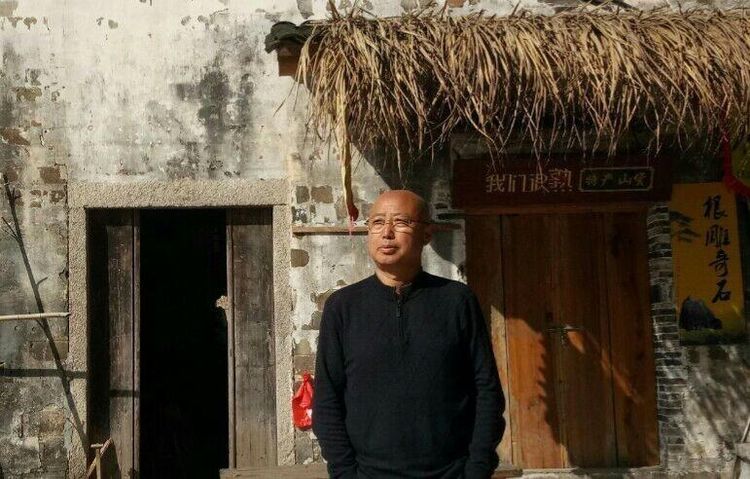东岭,母亲在这里长大。母亲告诉我,姥姥是破落人家遗弃的女孩,是被姥姥的父亲用扁担挑到东岭西边的房家沟,送给姥爷做团圆媳妇的。老爷父母早逝。姥爷勤快、吃苦、头脑灵活,积攒了几亩地。母亲说,她八九岁那年,姥爷在村东堑里那块地里种了很多面瓜和捎瓜。姥爷吩咐她看瓜。怎么看呢?母亲说,她看上了地头上的那棵大槐树。母亲小时候喜欢上树,爬树是她的强项,有了那棵树,母亲就有办法了。她来到瓜地看瓜时,双手抱树,脚蹬树干,连着几个上窜,就爬到了树上。她居高临下,瓜地尽收眼底,只要一有靠近瓜地的人,她双手做成喇叭状,放在嘴上“嗨”的一声大喊,那人马上就离开了……这是东岭上,在母亲地叙述中给我留下的母亲小时候最具活力的印象。
六十年代初,我们兄妹四人随在外工作的母亲来到姥姥家的村庄务农。姥姥家所在的房家沟村,它的东面有一道岭,村里人都叫它东岭。那道岭蜿蜒上百里,它与此刻我眼前的这道岭,一北一南,一脉相承。那个时候,我们兄妹四人在岭西边的姥姥家上小学,然后去岭东边的郭家哨读初中,后来在东岭一座“岭盖”上的沂南十二中念高中,整个的,我们兄妹四人是在东岭上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的时光的。
在姥姥家,我们一开始被安置在姥姥家后面的一座破旧的院落里。据说这个院子堂屋里的男主人上吊死了,家人都闯了关东,房子归了集体。这里的房子都是土打墙,盖房时村民们用少的可怜的几块青石做地基,屋墙、山墙、院墙,全部用黄沙土做材料,靠一块不大的光滑的木板,由人工一层一层地拍打而成。
我家住的那座老屋,墙上有几处裂缝,裂缝最大处白天能从外面透进光来。晚上,尤其是冬天的晚上,寒风时常吹着口哨,夹带着雪花在屋里盘旋。每当这个时候,睡在床上的我,都会用薄薄的棉被捂起头来,但那风像是着了魔似地闹腾的更加厉害,往往直到天亮时才会歇息。
我家老屋的院墙有几处缺口,晚上时常有野狗窜进院内,母亲便把一根手腕粗的木棍放在床头。晚上,尤其是妹妹肚疼呕吐后,会有多条野狗翻墙进来,一起对着屋门嚎叫,甚至用锋利的爪子抓的屋门嗤嗤作响,吓得我们兄妹四人不敢吱声。这个时候,母亲指着床前的木棍告诉我们说:“不用怕,有它在。”然后,母亲拿起木棍来到紧拴着的屋门跟前,她用双手攥住木棍,向屋门下面的过石上用力捣了几下,发出砰砰的声响。还真管用,外面的野狗竟没有了动静。
后来,我上初中时,每天早上我都要背起书包步行翻过东岭,去岭东边的郭家哨联中读书。那时感觉东岭很大,早上,上学路过东岭时,我都习惯性地站在岭上,回过头来看一看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庄。这时天刚放亮,偌大的村庄竟成了一片模模糊糊的树林。再向西望去时,远处延绵起伏的群山中,有许多非常明亮的灯光在闪烁,后来得知那是沂南金矿的灯火。那个时候,每当看到这些时,我的心中总会萌生出许多幻像来,而且那些幻像每每潜入我长夜的梦境。
村庄的夜晚十分安静,站在村头遥看东岭时,常有许多忽明忽暗、飘忽不定的光点在岭上游荡,大人们说那是鬼火,吓的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晚上几乎不敢出门了。东岭很大,向南,向北望去,一眼望不到尽头。东岭上有一种石头,那石头有得只有手指肚大小,石质十分绵软,我们都叫它“滑石”。上小学时,我们时常去岭上拣“滑石”,用它当作石笔,在方形的黑色石板上写字。后来全国“农业学大寨”,东岭被称作长虹岭,我们十二中同学们被学校组织在一起,由老师带队,住在长虹岭上的黑牛石村参加劳动。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参加了超过我们体力承受能力的深翻土地活动。坚硬的冻土,一镐一镐地下去,不一会手上就磨出泡来。晚上我们住在村民闲置的没有安装屋门的新房内,早上去汪塘边砸开坚冰,洗脸、刷牙,开饭时,吃着自带的煎饼。大概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回到家后我病倒了,是母亲昼夜守护在我的床前。母亲说,那期间,我多次从床上坐起,浑身颤抖,说着胡话……
东岭,它北起沂水县,穿过沂南县的东部,向南延伸至当时的临沂县汤头一带。我和东岭应该是有缘的,1991年的那个初冬,一纸调令下来,我从县城来到了东岭中段的大王庄乡工作,那个地方和我姥姥家东面的东岭相距不足三十里。当时,从县城来到这个偏远的只有一条窄窄的黄沙土路连接着的由几排孤零零的红瓦房组成的乡政府时,心中陡然生出一种落寞感。但值得庆幸的是这儿的人好。从乡里的干部到村里的村民,他们没有一个拿我当外人的,一年工作下来,我反而不舍得离开这个地方了。但两年后,又一纸调令下来,我还是离开了这里……
今天早上,我突然萌生了去大王庄看一看的念头。电话联系曾在大王庄乡一起工作过的宋弟,不巧,他有别的事情要做,脱不开身,我就自己开车来了。本来车上是带着相机的,我想着拍些照片作为留念,但当停下车来,看到村民们在田野里忙碌的身影时,我打住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身背这么大的相机有点太过招摇了,就没动那相机,只用手机随意拍了几张照片。
沂南2000年撤乡并镇,大王庄乡已经撤销二十多年了,如今属于蒲汪镇管辖。当时的乡政府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能够确定乡政府方位的是路东与乡政府对过的农村信用社,它能让你确信对面那片满是楼房建筑的地方就是当时的大王庄乡政府大院。沿着中心大街向北不远处路西是大王庄中学,当时中学的院子很大,操场很大,我曾去参加过一次乡村农民运动会开幕式。当时,身为大姐的赵春婷副乡长组织了这次运动会。期间,赵大姐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和整个运动会的热烈场景,让人印象深刻!那个时候,大王庄中学的教室、办公室都是平房,它是乡里靠集资建起来的,遗憾的是学校建起来后,学生小中专考试却没人能够考上,因而乡里流传着“花了100万,买了个大鸭蛋”之说。很快,学校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第二年就有许多学生考上了中专和高中。新校长上任后,我和乡政府的李兄曾到中学听过两次课,当时学校的学习氛围很好,从校长、教导主任到老师和学生,在他们的身上都能让你感受到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
如今,大王庄中学原有的平房早已被楼房取代。我停下车来,在中学大门前站了一会。校园很静,没见有任何人走动。我突然又想起那个时候的大王庄中学来,想起那个时候的老师和学生们,如今他们大都不在这里了,那时的学生也都成为老师了……
从大王庄中学往西,跨过高速公路是泥泉官庄村。过去曾听朋友说,在泥泉官庄村通往中学的路上有一座小石桥,那桥虽小,却有些岁数,在桥下涵洞两侧的青石上刻有一对龙的图案。因而,我的思路从这里开始,沿着一行深深的脚印,寻着一个奔跑的身影,进入了这个村庄……
从大王庄中学到泥泉官庄村这段路上,有两条一大一小的河沟。两条河沟其实都不算大,但却有水,而且那水是长年都有的。此刻,岭顶上,那水在不引人注意的水草中隐隐地闪烁着,那闪烁仿佛在告诉我,那龙一直都在。今天,我先后沿着两条河沟寻找多时,其中的一条河沟,我甚至找到了它的源头,最后发现那座雕刻着龙的图案的桥已经被新建的桥覆盖了,但那桥还在,那老桥的石头依然清晰可见,那龙的确还在。
一个人一生中会去过很多地方,但最难忘却的,无论怎么走也走不出来的,也许就只有一处,那就是故乡了。那里也许以一条河,一座山,一道岭,或一座城,一个村庄,甚或一间老屋,一棵树为坐标,但那里,一个人的魂注定就住在那里了。东岭,我想这就是我的故乡了,这地方虽小,但小有小的好处,它能让人更真切的听到自己地呼吸,感受到自己地心跳。那地方固然闭塞,可它宁静。
东岭,这些曾经一律用泥土、木棒和麦秸构筑的村庄,这些如今让人看了心疼的残缺的老墙,深邃的老井,光滑的老碾,窄窄的街巷……看到它们,我又想起了母亲。那年我在郭家哨联中读书时,有天刚下中午课,老师告诉我说,我母亲给我送水来了,我腾的一下脸红了。那天,我母亲怕我早上吃的饭菜太咸,中午,母亲提着暖壶,拿着一个瓷碗,翻过一道岭,步行8里路来到学校。我怕同学们笑话我,没有出来见我母亲,母亲又把水提回家了。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我流下了眼泪,我后悔没有勇气出来见我母亲一面,一直后悔!
那时父亲在外工作,整个家庭重担母亲一个人挑着。推磨,推碾,烙煎饼,炒菜,做衣服,浇园,干农活,这些都落到了她一个人的肩上。尽管这样,母亲的神色一直很安静,直到现在,一直很安静,安静的如同村庄的老墙和墙角的油菜花一样。如今,年已九十岁的母亲,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我永远不敢惊动母亲的神色。
东岭,这里一片寂静,一片安详。1959年筑起的大坝,1977年贯通的水渠,它让人熟悉,又让人疑惑,我想去那个久违的涵洞看一看,顺便制造一场穿越时光的飞翔。一位老人问我,你看那涵洞干什么,我微微的笑了笑,遮住了心中的澎湃与感激。东岭,这里承载着数不清的记忆,那些难忘的经历和体验将会留住。那不仅因为一时的激动,也不仅因为偶发的颤栗和冲动,更不是那些说不明白的心情和情绪。我很清楚,我的魂魄注定就住在这道岭上了。东岭,这岭上的老屋,这岭上的每一粒沙土,每一滴水,注定与我和我爱着的亲人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