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农民诗人尤克利
E788.冯春明:一个想家的人

——尤克利近照
忽闻河南特大暴雨,一下子想起尤克利来……尤克利用微信留言告诉我说:“兄长放心,我在” ……
尤克利去河南打工一年多了,很少见他回来。一场史上没有过的大雨,更让人放不下心来。想尤克利时,读克利的诗,这是我多年以来形成的一种习惯。尤克利打从十七八岁时起,就从家乡沂南出发外出打工了。常年在外打工的他写了好多诗。那些诗像山坡长出的小草,像各色各样的野花,更像月夜随风飘落的花瓣,时常把我的睡梦打醒……
今晨醒来,尤克利的《把梦想说给你听》这首诗从微信朋友圈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向我走了过来。他的诗很像他的人,很远却又很近,朦胧却又真实。而今,因为一场暴雨,我向着他,他向着我……继而,我向着他的那个方向,向着那个方向的那片布满乌云的天空格外多看了几眼……这时,一个声音由远而近、由小而大地从那片布满乌云的天空中缓缓而来……“那是低处的/企图走出沼泽的腿脚/石缝中攀援的手臂/鱼在水草中吐出的泡泡/梦想着有朝一日众生平等”……
这又是那个漂泊在外,游离家乡的人的声音啊!这是尤克利。这是一直不善言辞的尤克利。他让他的心灵于云幕中穿连起了许多数不清的气泡,以至于让我的这个早晨如梦似幻。他说:“在你看来/这哪里算得上是梦想/简直是一颗颓废的不思进取的可怜之人的可恨之心/可我郑重地对你说,这就是我的梦想”……是的,这就是“我的梦想”,这就是克利兄弟的梦想啊!这一刻,克利似像是在托梦给我。但见,窗外的那一缕缕微光,竟像满月之夜里的那些不断飘落的梨花纷纷扬扬了起来。
是的,“可我郑重地对你说/这就是我的梦想。”嗯,是的,因为有了克利兄弟,嗯,一直因为克利兄弟,我竟感觉到了一种源于大地而又超越世俗的存在。我也因而在他的诗歌戛然而止处,萌生出一种莫名的感动,并明显的感觉到这种感动充塞了清晨的大气!
对许多人而言,尤克利也算是个名人了。然而,多少年来,他却一直不好意思抬起自己的头来……打工的路上,他所能做到的只是把他的诗歌,把他的命运,把他的思念,把他的向往,小心翼翼地编织成梦……
尤克利出生的村庄就在我家西面一个人称杨家道口的地方。童年的记忆里,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其实那地方离我并不远。我所住的村庄在沂河东面两座丘陵间的凹处,距离尤克利的村庄杨家道口不足十公里。人们进城需要翻过西岭,经过杨家道口。杨家道口在沂河东岸,那是进城的必经之地。来来往往的人们,靠一艘木船渡河。
杨家道口,一年四季撑船人不知疲倦地撑着小船将人们送过河去又接过河来,清澈见底的沂河水,长年晃动着他们的影子。冬天来临,当大人们从城里买回山里的柿饼、软枣、栗子、花纸和鞭炮时,孩子们便欢呼着,蹦跳着,迎接着又一个新年的到来了。每当这个季节,每当年关切近的时候,总有三两个人到周围村庄“凑侍奉”。“凑侍奉”是村里人对那些撑船人到村里收费用时的一种称呼。村里的大人们见到他们都像老朋友一样热情地打着招呼,有的从家里端出一瓢大豆,有的拿出几个鸡蛋,有的拿出家中的花生、地瓜……那些“凑侍奉”的人是杨家道口的撑船人。平时,他们不收坐船人的任何费用。只有等到年底,等到新的一年将要开始的时候,他们才推着小车到周围的村里凑一次“侍奉”。“侍奉”多少不限,即使家里穷得拿不出东西的人也照常可以坐船。我与尤克利相识后,这是我们经常谈起的一个话题。
尤克利是个诗人。我第一次知道尤克利的名字是在1991年的《鸢都报》上读到的。当时,报上推出了尤克利的一组诗歌。读后,我被尤克利诗中浓浓的情所打动,随即有了见一见尤克利的冲动。不久在刘京科兄的介绍下,我在沂河岸边的一个菜园里见到了一脸腼腆的尤克利。
尤克利的家就在平展的沂河冲积平原上。当时,那里被一堆堆黄灿灿的时隐时现的沙丘所环绕……村庄的周围到处长满了茂盛的庄稼、蔬菜和果树。村子很静,我和京科兄坐在尤克利家的院子里时,那静,静得几乎能让我们听到河水流淌的声音了。那个时候,在那里,我们数次交谈于布满沙滩的河床,数次在清清的沂河水中畅游……我们多次吃过尤克利菜园里的黄瓜、西红柿和果园里的苹果……
后来,尤克利外出打工了,他去徐州,去河南,去广东;最远处,到了日本的北海道。自那以后的日子,每当想起尤克利我就会想起沂河,想起沂河岸边的蔬菜、庄稼,想起沂河西岸的灵山,想起小时候大人们从城里买回的柿饼、软枣和栗子,想起到我们村“凑侍奉”的撑船人,想起朴实、憨厚、热情又不乏内秀的尤克利和他铇蘸思乡之情的诗歌。
尤克利和他的诗歌与这片土地联系得太紧密了。读着尤克利的诗,握着尤克利的手,你无法想象一个曾飘洋过海去日本种菜,目前,仍在河南打工的他会与这片土地割裂开来。是的,每当尤克利离开这片土地时,他的家乡也跟着他一起去了。远走它乡的他走的越远,心与家乡的这片土地越近!他走的越远,家乡在他的意象中越加浓烈,更加清晰!他因为想家,开始写诗了……
“我思念家乡的方言/去徐州车站听乡音” ……这是尤克利在徐州打工时写在他的诗歌《去车站听乡音》中的一句话。常年打工在外的尤克利,他太想念家乡了!在异乡的车站,他蹲在一个人来人往的角落。他不坐车,他只希望“客车运来一万句方言/灌满自己的耳朵”……是啊,异乡只是脚下的一个站点,在这些充满喧闹,充满幻想的地方,又有谁会在意一个想家的人呢?所幸,在车站他不再孤独,南来北往的车,来来往往的人群,偶尔会传来一两句熟悉的乡音来!听到乡音的他,“感恩地献上两只杯子/黄色的是啤酒/淡黄色的是新沏的茶”(尤克利诗《去车站听乡音》)……
尤克利的性格是内向的,他更不好意思让人知道他是多么的想家。是的,一个男子汉的思乡之情又如何示人呢?他在诗里写到:“去车站听乡音/请不要看见我/一个貌似坚强的生鸡蛋/被想家的念头轻轻一碰/流出没出息的泪水”(尤克利诗《去车站听乡音》)。是的,他流泪了,然而,正是这“没出息的泪水”,正是这种细腻的、触及心灵的真情实感,使他成为活跃在当今诗坛上的一位著名的农民诗人!正是这熟悉的乡音在他精神与灵魂孤独无助时,成为他真正的依靠和寄托。
在我的生活里,自从尤克利以思乡游子的身份出现在我的眼前,出现在与我的生命息息相关的视野里时,我再也无法忘记他了。每当家乡的文友们聚会时,我总忘不了给他打个电话,并让文友们轮流跟他说上几句话。每当这个时候,我发现身处异乡的他,总在静静地听着乡音……
一天,远在广东河源打工的他,想家想的几乎要发疯了,他跑到河源的一个山坡上,他发现河源的天空下全是山!他用上所有的力气,一步一步地登上山顶。他向着家乡的方向望去……他大喊:“我要让河源所有的山/与我一起扭头向北/看一看我的家乡沂蒙山”……读到此处,读到这首诗时,我的意象里河源所有的山仿佛真地动了起来,我仿佛听到了广东河源那一座座大山扭头向北时,自颈部发出的震撼人心的轰鸣声!是的,每次通过克利的诗歌,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时,我发现尤克利的诗歌之树是深深扎根在他生命意识的深层的,它的每一条根都紧紧地联结着养育他的故土。他的诗也因而每每引起读者的共鸣!
由于常年外出打工,尤克利没能回家和母亲见上最后一面。黄土下的母亲成了他一生的愧疚和牵挂!母亲走了,母亲在地下安家了……望着草丛中孤独而立的坟墓,他说:“那些在老家的春天里/为母亲采集草药治病的好人/你们是孝子/但你们要听我的恳求/不要去我母亲的坟头/采那些正在开花的甜酒根……”(尤克利诗歌《思念的花朵》)。是的,这是诗人对那些采药人地嘱咐,他怕采药人一不小心惊着母亲,惊着那颗脆弱的心。
母子情感是一种最具个体特征的感情,也是最能呈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情绪的爆发点。尤克利诗歌《思念的花朵》中,诗人面对“为母亲采集草药治病的好人”时,几乎是用哀求的方式了,他“祈求善良的采药人/别惊动了那片甜酒根。”他要让“它们的花静静地/静静地/在母亲的坟头开放”……这里,诗人以至真至纯的情,以盈盈欲滴的泪,以朴素无华的语言,让母子之情在纯朴的“自私”里,闪烁着真挚的人性光芒。
意象是诗歌艺术的精灵。尤克利的诗歌意象具有成熟、贴切、内涵丰富的特点。他的诗歌《我知道》,其中的意象明显具有亲切、深刻的特质:“我知道这世界上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鸟/他都不是孤独存在的/为了命运的路途/蜗牛背着房子/蜂去采蜜/蛇省略了脚/青蛙冬眠/龟隐须臾的幸福留住/四十年光阴/我小隐于野”。不难看出,这是一首具有厚实生活底蕴,触及生存环境的一种生命地低吟。诗歌中所嵌入的背着房子的“蜗牛”、采蜜的“蜂”,都是极具生命本色的流露,处处蕴含着独到的诗歌意象。
尤克利深沉而不乏内秀。尽管他的脸上每每含着笑,但在他的眼睛里,在他的诗歌里,分明深藏着一种伤感与悲悯的情怀:“深秋辽阔的田野上/一场细雨在倒下的玉米地里下着/那么均匀/细致入微/但沉默的玉米已不需要滋润/人们已经取走了它腰间的牵挂/那些叶子也不再鼓掌……”(尤克利诗歌《深秋》)。尤克利的诗歌《深秋》,这是一种极其沉重的意象对话!静静的深秋,灰色的天幕细雨无声,诗人站立在深秋静谧的旷野上……他怅然若失地回忆着曾经的繁茂,悲悯的目光表达着对现实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和对生命深处的凝眸与沉思……
“家乡的树木还在生长/我在它们中间潦草地穿行/不知道哪一棵最终和我的缘分最深/情意最重/困顿的时候/设想一下身后的日子/时间永恒/纸醉金迷/还有一棵树/愿意像爱人一样陪伴我/一起慢慢腐朽/想想都是福/想想都是天机/有时候我抚摸一棵粗糙的树/如同抚摸我自己”……这是尤克利的诗歌《家乡的树》,这首诗虽然仅仅就是那么几行字,但读后却让我如梦初醒。因为它把我忽略了的事物倾刻间锻造成生命深处的声音了。这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人的生命中原来有一棵“像爱人一样”的树,它“一直默默地陪着自己成长,并默默地陪着自己慢慢腐朽。” 是的,人很幸运,最终还有一棵树陪着你……我真想找到这棵树!却找不到……这棵树的确已经在那里了,但它不告诉你它在哪里……我突然喜欢起树来,就像诗人在诗中说的“想想都是福,都是天机,有时候抚摸一棵粗糙的树,如同抚摸自己”……
尤克利生于沂河边,长于沂河边,对沂蒙山的父老乡亲,对这里的山水树木、庄稼蔬菜、猪狗牛羊有着深厚的不可言说的感情。长期的农村生活形成了他特有的农村情结。他以大地为琴,沂水为弦,将村庄紧揽怀中,用深情、灵动的诗歌倾诉着他与乡村的不解之缘:“用三月的柳笛/唤回沂河两岸的绿/用一把瘦小的秧苗/ 抒写百里画卷/鸽子带着少年的理想 /在天空盘旋/这就是我们的家 /我看见了牛羊走上山坡 /风吹草低/九曲的沂河 /舒缓/豪迈/回望着走远”(尤克利诗歌《沂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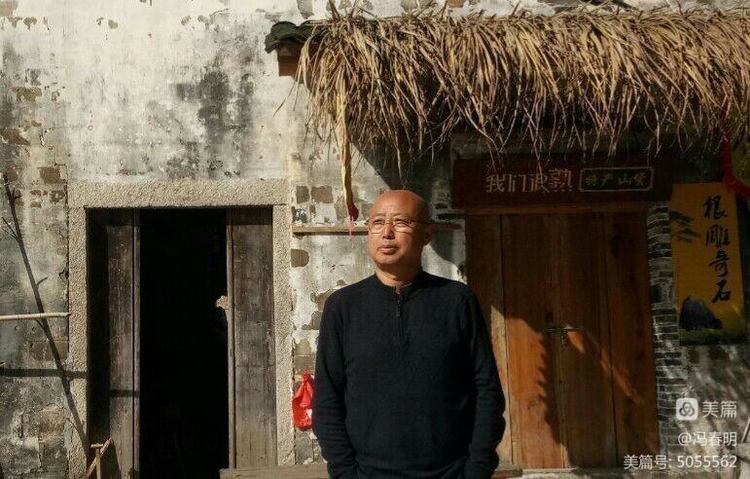
冯春明,1959年生,山东沂南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有散文、诗歌、文学评论见于《山东文学》《山东作家》《前卫文学》《时代文学》《当代文苑》《青岛文学》《延河》《九州诗文》《诗刊》《星星》等。著有散文集《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