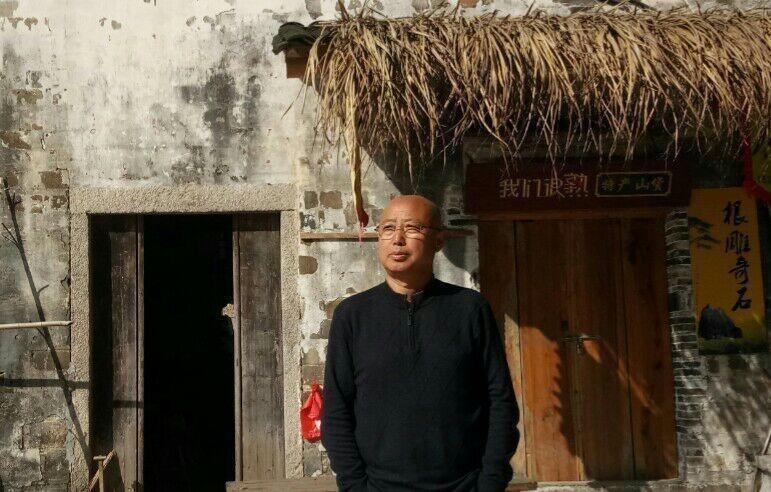无论怎么说,我想,我与刘淑愈这个人还是有缘的。昨天,当我翻阅《临沂历史书院》一书时,书中介绍的临沂地区明清时期设立的28个书院创始人中,最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那个从波翻浪涌的漩涡中走来的刘淑愈。他因此而吸引了我,以至于让我好长时间走不出他的背影。
所以,今天一早,我就约许嘉鸿兄一起驾车前往刘淑愈创办的书院所在地——费县探沂镇的岐山;开始了寻访刘淑愈的旅程。从沂南县驾车去刘淑愈创办的那个“岐山书院”,约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整条道路,路况一般,甚或说路况较差。路上,岔道很多,多亏GPS导航,拐了许多弯,直到跨过祊河后,又行驶了一段路程;然后穿过好几个村庄,才望见岐山。
岐山,从远处看去并不算高,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雄奇险幽之感。是的,远观岐山时,它的那道绵延起伏的黛绿色的山脊,反倒透着一种温柔和秀气。顺着山道,我的汽车很快来到岐山跟前。我把车子停在岐山寺前的一片空地上。
刘淑愈创办的岐山书院就在岐山寺内。由于岐山寺处在一个类似于“座椅”或“簸萁”形状的山峪中。所以,当地人把这座山称作“萁山”。至于“岐山”这个称呼,大概是那帮在这里读书的文化人叫起来的。“岐山”其实在陕西,原称“凤凰山”,取周文王“凤鸣岐山”之意。“凤鸣岐山”的典故由来已久,它说的是周王朝行将兴盛前,岐山有凤凰出现。人们认为,凤凰是由于周文王的德政才来的;岐山有凤凰栖息鸣叫,那是周王朝兴盛的吉兆。
眼前,位于费县的这座“岐山”,它的名字叫法很多。清朝时候,也曾被称作过“旗山”。“旗山”这个称谓是否与刘淑愈武装据守过这座山有关,不得而知。然而,现在的岐山寺,在寺庙大门的匾额上干脆题作“其山”了。岐山称谓很多,但是发音相差不大。我想,还是以当下官方使用着的这个“岐山”二字为准吧。
岐山之所以吸引我,不仅在于刘淑愈创办的书院,也不仅在于他揭竿而起之后的那些故事,更在于他这个人,以及他在这里留下的文字。刘淑愈是清朝道光年间的进士,他不仅是创办“岐山书院”、教授生徒的那个刘淑愈;也不仅是竖起反清大旗,率众起义,后来成为“岐山幅军”总军师的那个刘淑愈。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像刘淑愈这种“进士造反”的人是极其罕见的,他的确是中国古代“进士”当中的另类。
当年,刘淑愈教授生徒的岐山书院,就在现在的“其山寺”这个位置。刘淑愈创办的书院虽然在战火中损毁了,但是那三棵一雄、双雌的千年银杏树仍在。那是刘淑愈在这里教授生徒时就早有了的。如今,这三棵历经火烧雷击,伤痕累累的大树,宛如一个个饱经沧桑的文化造型,坚挺的站立在那里。它们粗壮发达的根系紧紧地抓住山里的石头,深深地扎入厚重的泥土和窄窄的石缝……岐山之下,银杏树郁郁葱葱的树冠,粗大的树杆,黑黝黝的石头,暗红色的土地,让三棵大树整个的与这座山脉融合为一体了。看到它们,更让我想起刘淑愈。
眼前,这座近年来重新修建的寺院稍显单薄。但是,尽管这样,已属不易。据说,初次来这里重修寺院的和尚,在开始施工时的一个晚上,被人装进麻袋扔到很远处的一个山沟里。不过这位被人解救后的和尚初心不改;他毅然返回工地,直到修成这座寺院。进入寺院后,许嘉鸿兄与寺院住持进行交谈,我沿着寺院西面的山坡向山顶爬去。我是想以这种攀登的方式,用我的双脚一步一步地从这些坚硬的石头和草木中,去感受隐秘在这座山里的故事。
真想不到,这座看似不高的山竟然很高。整个登山的过程,让我气喘吁吁,中间歇息了数次之后,才接近当年“岐山幅军”遗留下来的那片已经坍塌了的寨墙墙基。后来,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岐山海拔高度有四百多米。
岐山山顶,树木稀疏,荒草凄凄,四周全是大块青石砌成的残垣断壁。乱石之中,我踏踩着悬空着的石块,穿过荆棘的缝隙,登上山顶北侧断崖上一块巨大的石头。站在巨石上向北瞭望时,远处,层峦叠嶂,绵延不断的莽莽群山尽收眼底。那是一种看上去让人心旷神怡的画面。
突然,一股强劲的寒风迎面袭来,吹了我一个趔趄。这风好像是有意的,它像一位多年不见了的老朋友,见面后猛然向着你的肩头来了一拳!这一“拳”,恰于恍然中开启了我的思路。我开始在我的大脑中搜索着刘淑愈这个名字,搜索着岐山寺大殿重修时,刘淑愈所作的那个《碑序》:
余尝偕二三贤士大夫,登旗山之颠,慨然而动遐思:东望艾山,则柳毅神君传书处,又其东,抵琅琊,为汉武乡侯、晋王右军故里;转而北望,蒙山在焉,山之下郁郁乎、苍苍乎,是唐颜常山、颜鲁公三昆仲坟墓。苍松古柏,历历可数,非惟人杰,山亦有灵,假使诸先政而在,虽为之执鞭所欣慕焉。
刘淑愈所题《碑序》意境深远,气势磅礴。文如其人!其情其景似在眼前。先生真乃才华灼灼,抱负远大,英雄豪迈!
这个《碑序》应该是刘淑愈在岐山创办书院那段时间写下的。从文字中完全可以看出,沂蒙大地山水人文之于刘淑愈内心的辽阔和大气!我想,刘淑愈与他的朋友们,当时应该就是站在我站的这个位置瞭望群山的。此刻,这些历史曾经的光影距我如此之近!他们给我的感觉已不再是那些匆匆过往的孤独流浪于时空中的过客了。刘淑愈的身影因了一段文字,因了一种豪迈,因了一种情怀,已经深深地刻印在这座大山之中。这其中有文采,有思想,有温度,有胆识,有血性,更有中国历史上真正文人的那种硬朗强健的风格和诉求在那里。同时,它也让我看到了沂蒙历史文化的厚重和清末体制下荒苦、寂寥、没落的无情延续。
风突然停了下来,山野一片寂静;四周懵懵懂懂,恍如梦境。这时,恍惚中,有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的刘淑愈,仿佛站在了我的面前……大山之上,在这个冬日的暖阳下,我庆幸有机会与他完成了一次跨越百年的对视!并有机会仔细打量一下他,从而获得一种刚劲、深厚又不乏细腻、清新、率真的感受。
显然,站在这里的刘淑愈对腐败的清王朝彻底失望了。于他而言,大山之上的凝思意味着一场神圣的洗礼;它赋予了他的生命以新的索引。因而,也就有了后来他在“岐山幅军议事堂”所作的两副楹联:
一
南朱雀,北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恰成旗山阵势;周姜尚,汉诸葛,唐李靖,宋武穆,居然名士风流。
二
东狩获麟,食其肉寝其皮;中原逐鹿,大者王小者霸。
刘淑愈,祖籍今兰陵县横山乡沈坊前村。明末,刘淑愈祖上迁至费县毛家河村。刘淑愈生于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他“自幼聪慧,记忆力超强。”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举人。道光六年(1826)中进士。他由于“不会投机钻营,仕途蹭蹬。”直至道光十九年(1839)才被授予顺天府房山县知县,且任职仅百日,即因“不谙政体,难膺民社”而革职。后朝廷以“该员文理尚优,可任教职”为由,降为泰安县教谕。任职不到半年,又因“触怒权贵”遭弹劾,刘淑愈愤而辞职回乡。
辞职回乡的刘淑愈反而轻松了许多,但人是需要有一个远大目标的,而他心中的目标就是“文化”。“文化”这两个字在他的心目中,概括为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坚守。很快,刘淑愈来到了香火旺盛的岐山寺,他与住持僧空仙结为好友,在岐山寺正殿开办了书院。几年下来,他的学生有四位先后考中进士,另有进学、中举的学子难以计数。
刘淑愈创办岐山书院后,那该是他人生中最为美好的一段时光了。这期间,在岐山书院,在那三棵古老的银杏树下,他把他的知识手把手地传授给他的学生们。这也让在精神素养上、学识素养上、道德素养上,有着高蹈境界的他,有了用武之地。
然而,好景不长。太平天国起义后,天下大乱,刘淑愈不得不解散书院,居于家中。咸丰十一年(1861),面对腐败没落的清王朝,刘淑愈竖起反清大旗,率众起义。他亲自手书讨清榜文,“传示蒙山之阳抱犊之阴,有众数十万”……这次起义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同治二年(1863),清廷调集山东兵力进行围剿,刘淑愈在岐山固守被俘,后在狱中被害。
又一阵山风袭来,天慢慢的变得阴沉了起来。这个时候,我踏着一块块坍塌的围墙乱石,沿着山脊由西向东,慢慢行走……脚下,荆棘丛中悬空着的石块时不时的左右摇摆,我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地,感受着一个人在最惨伤,最困顿,最郁闷,最灰暗的阴影中曾经走过的路。此刻,整个的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历史漩涡中……瞬间,我被一种悲壮而传奇的气息;被一种自由、独立和完整的个性所感染!我仿佛看见曾经武装到每一个山角的山寨和银杏树下那座书院的影子;仿佛听到了分别从山顶和山下两个不同的方向传来的号角声和读书声!
清末,在岐山,在一段灰暗的历史阴影中,“书院”与“山寨”,“读书声”与“号角声”,它们在同一座山上,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上演了极其矛盾又极其真实的一幕!岐山,这个座椅状的山中上演的一幕,是历史长河中十分罕见的一幕。他让我真切了解到历史长河中生成的一个人的悲喜真相!
再见了岐山,再见了刘淑愈。回来的路上我想了好多!刘淑愈走了,刘淑愈的确走了。但是刘淑愈的身影却以一座山的形象永远地站立在那里!我想,我们的民族能够从没落的清王朝废墟上得以崛起,恰恰是因为那个时代有了一批像刘淑愈这样有骨气、有思想、有文化,有追求、有情怀、不怕死的人!是他们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