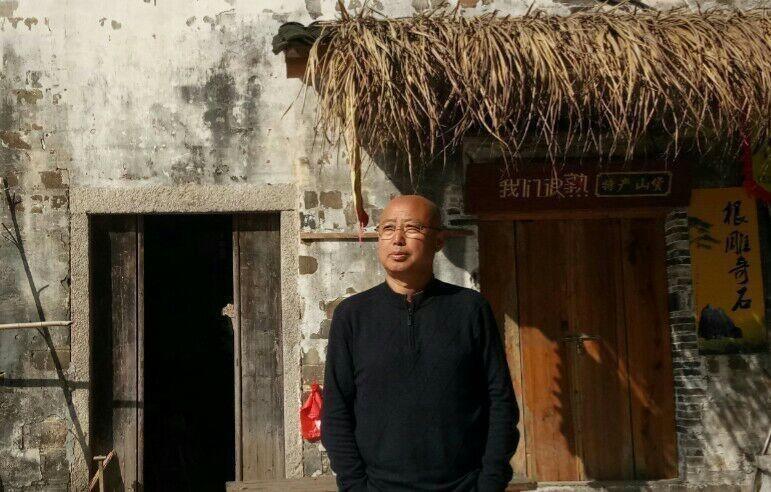我一直庆幸自己没有离开沂河,并且能够自始至终地生活在被沂河滋养的这片土地上。我开始上小学的那年,随母亲去了沂河以东姥姥家的那个村庄定居。姥姥家在两座南北走向的大岭之间。村子被一条大沟隔开。沟东、沟西一分为二。沟西地势较高,大多是马姓人家,人称马家崖头;沟东地势较底,有杜、邹、李崔、徐姓等等,人口多于马家崖头,人称“庄里”。大沟常年有水,水不大,但却清澈。下大雨时,沟里的水开始上涨,每当这时,有成群结队的小鱼逆流而上,有的小鱼甚至沿着雨水形成的径流,游到街巷里来了。
雨过天晴,雨水退去,有些来不及撤离的小鱼滞留在洼地。那鱼有着各种各样的颜色,白的、黄的、黑的、红绿相间的……这些游在浅水里的小鱼,看到有人过来时,就在露着脊背的水里横冲直撞了起来。母亲说,那里面的鱼,有的是从大河里游上来的。
姥姥村庄的那条沟与大河相通,母亲所说的大河就是广为人知的沂河。见到沂河是我七岁以后的事了。有年妹妹生疹子,高烧不退,父亲骑着自行车,带我去沂河西岸的大成庄,找一位专治疹子的名医抓药。父亲沿着村西的一条小道,爬坡上坎,翻过西岭。岭西是一片开阔的平原,路也宽阔了起来。待穿过几个村庄之后,路边出现了好多沙丘,不一会儿工夫,有一条宽阔的河流出现在眼前。河水看起来很深,河的中央有一条木船向着我们这边划来。父亲说,这就是沂河。
河边,等着坐船的人很多。送过两船客人后,轮到我们上船了。撑船的老人把船停稳,放下踏板,父亲踏着踏板,先把自行车抱到船上,然后领我上船。不一会,船开始离岸。那是一条不大的木船,撑船老人手握长篙,立足船帮,眼望前方,用力撑起船来。行船时,船首荡起朵朵水花……撑船老人伴随着水花的声响,哼起了歌谣,那歌声浑厚而悠远。
这时的沂河,水面不是很宽,沙滩占了河床的大部,不一会儿功夫,船就到了河的中央。站在船上,可以眺望河流上游的远山,往下看时,河水并不算深。那水清澈见底,你不仅可以看清水下的鱼虾、河蚌,还可以看清河底上的沙子。船停下来后,需要在河滩中走上一会。河滩上有着许许多多的,被来来往往的人们留下的,大大小小的脚印和车辙。那些散乱、重叠地分布在沙滩上的脚印和车辙,紧紧连接着结实的土地,它为人们凝塑成一条生命不息的川流。那次路过沂河,是我记忆里最深的一次。
七十年代末,我被分配到沂河东岸的苏村公安派出所工作。这个时候,沂河渡口已被正在建设中的沂河大桥取代。渡口虽然不在了,但从乡亲们那里,还是能够听到一些有关于沂河渡口的故事和传说。老人们说,古时候,沂河南来北往的船很多,大户人家盖房用的杉杆,都是通过沂河从南方水运过来的。沂河上游的货物,也是通过沂河运向南方。夏季,发大水时,时常有蛟出现。那蛟眼如明灯,若隐若现。据说,一旦蛟的身子横了过来,河水随即上涨,甚至涌上岸来。这个时候,村人们烧纸上香,磕头作揖,那水才会退去。
沂河渡口也是过往船只中途暂停休息的地方。过往,有的船夫相中了这里的姑娘,干脆留了下来,在这里安居乐业了……亘古至今,沂河水在静静地流淌着,多年以来,我曾无数次地想象着沂河,想象着这条与我生命密切相关的河流中,那些曾经的过往;想象着它所走过的那些路,那些地方;想象着它走过的那些路,那些地方的模样。
2012年的秋末,一次文友聚会,我有幸走近久违的郯城县马头镇,并登临镇驻地北面的沂河古码头防洪堤。登上防洪堤向北望去,古老苍茫的沂河水,以一种开阔宏大之势,由北向南缓缓而来。这是来自家乡的水,这是来自我童年记忆里的水!霎那间,有一种久违了的温润而熟悉的气息迎面扑来。河水走的很慢,慢的几乎看不出脚步的频率,但河水的确来了,的确来到我的眼前了。是的,河水来了,它走的很慢,它带着我童年的梦境和家乡的那股乡土味,缓缓地走来了。它走的很慢,并且在我的眼前骤然停住。它停的那么安静,安静的没有一点声音。沂河水——难得这跋涉数百里之后的歇息。我感叹,感叹初次来到马头的我,能与沂河一起在这里相聚,在这里入梦。
稍后,沂河水又开始启程了,它以九十度的指向,开始向西流去。马头——在这里,沂河——在这里,它们于不经意间默默地完成了一个有力地转身。眼前,走过重重山路后的沂河,在这个宽阔、安静的港湾积蓄了它的力量后,继续前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生死变灭,有多少恩爱情仇,有多少重来与离去,有多少相关生命的笑声和哭声!沂河,它身后这湾古老的水域,像一个硕大的脚印,留下了一团团永远叙说不清的往事。
此刻,静静的港湾在阳光温暖地照射下烁烁发光;不远处,一对美丽的水鸟,正在水面上嬉戏。微风吹来,水面波纹悄悄涌动,恍如梦境。此情此景,恍恍惚惚。回望沂河过往,一眼清泉涌动,一丝天水落下……那水从源头出发,源源不断地,自上而下地,一路跌跌撞撞地跳过山涧,流过旷野……河边人们,曾几度面对高山长啸,几度静听山鸣谷应,又叹韶华不再,青春逝去!
此刻,待我抬头向北望去时,那一波波来自上游的河水,悄然涌动着一股亘古不变,唯有河流才有的气息。那是一种蕴涵着生生灭灭,喻示着源远流长的气息……它让我仿佛看到了家乡的那条小河,看到了儿时伙伴们奔跑在时光中的碎影,并想起了许多温暖的往事,甚至隐隐听到了母亲河边洗衣的棒槌声。
沂河,我童年的梦。这时,道口撑船人不知疲倦地撑着小船——将人们送过河去又接过河来时的光影,又出现在我的眼前……记得冬天来临时候,当大人们从城里买回山里的柿饼、软枣、栗子、花纸和鞭炮时,孩子们便欢呼着,蹦跳着,迎接着又一个新年的到来了。每当这个季节,每当年关切近的时候,总有三两个人到周围村庄“凑侍奉”。“凑侍奉”是村里人对那些撑船人,到村里收费用时的一种称呼。村里的大人们见到他们时,都像老朋友一样热情地打着招呼,有的从家里端出一瓢大豆,有的拿出几个鸡蛋,有的拿出家中的花生、地瓜……那些凑侍奉的人是道口的撑船人。平时,他们不收坐船人的任何费用。只有等到年底,等到新的一年将要开始的时候,他们才推着小车到周围的村里来。“侍奉”多少不限,即使家里穷得拿不出东西的人,也照常可以坐船。
故乡的沂河,您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在这儿您没有了冲向山下的跌宕澎湃,您也许已经累了,是该休息一会儿了。此刻的我,轻轻地踏着大河的肩膀前行……脚下,河堤层层叠叠的石板,如同大河的肋骨,紧紧守护着河流的胸腔。清晰可见的古码头台阶,自河面而上,似在诉说着曾经的繁忙和那些曾经的故事。
立足河堤,向南望去,一条笔直的古老街道,贯通小镇南北。过往留下的残垣断壁,隐隐着一股深沉、厚重的气息。河堤下是马头有名的北水门牌坊。过去,人们从码头下船之后,就是经由北水门进入马头古镇的。
马头镇位于郯城县城西不远处。隋唐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马头利用依傍沂河的便利条件,联通京杭大运河,成为古代水路与旱路交通的交汇点。过去,马头上航可以直达京济,下行直通苏杭。随着商贸业的逐渐兴起,唐代已初具规模。清末民初至七七事变前,马头工商业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全镇大小商店和手工业作坊有三百余家,生意兴隆、市场昌盛,形成了郯城的商业中心,亦为鲁南苏北的一大商业重镇,享有“小上海”的美称。民国初年,山西晋商经营铁业的泰顺商号,有“泰顺的老鼠——盗铁”之说。诙谐的语言里隐喻着商号的兴盛。
马头是回汉民共居之地,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大多为寻找商机而来。当地老乡介绍:伊斯兰教明朝传入郯马地区,永乐3年在马头建清真寺。期间,“三清阁”、“文昌阁”、“山西会馆”和耶稣教堂陆续落地。百年来,它们隔街相望,和睦相处。具有独特风格的“淮调”“大调”“郯城满江红”“玲玲调”“大寄生草”等五大类民间歌曲,在这儿唱响了一部浸透着河流意蕴的民族融合交响曲。
马头,残缺的青砖绿瓦,古老的码头堤岸,依稀可见曾经的辉煌。繁忙的码头,沉重的脚步和着收获的期盼,离我们很远又很近。过往岁月,沿着大河而来的货物在这儿卸下,来不及歇脚,大船又装载着山里的特产流向远方,光荣与梦想在这儿汇聚,从这儿开始。
沿着河流的走向,向着历史望去,上游乘势而来的小船,正在清末民初的月光下南行。水手们遇到村庄时,不再像白天那样大着胆子,向着河边采桑的村姑吼上几嗓子了。村庄静悄悄地,一切静悄悄地,水手们坐在船舷,静静地凝视着天上那轮明月。这个时候,大河之上,人与时间和空间的漫游,在悲伤、失落、梦想和处处燃起希望之火的瞬间,诠释着不息的生命真谛。
天开始放亮,下游,一艘豪华的游船正在扬帆北上。来自杭州的大家闺秀,走向船头,好奇的看着沂河两岸的风景。此刻,古码头白帆片片,桅樯如林。岸边,一位肩挑水桶,踏着台阶拾级而上的诗人吟道:石头礓擦滑溜溜/上上下下度春秋……
又一天过去,风突然大了起来。早晨,人们惊讶的发现,河堤上长出了许多凉冰冰的刺刀。“鬼子来了!”各地商贾四处逃难。那天,马头古镇所有的银杏树落下了所有的叶子,大地一片惨黄……历史的瞬间,一场民族的灾难过后,是一场文化的浩劫。马头,古老的店铺,繁华的街道,在无奈中湮灭。
眼前,沂河水在缓缓地流淌着,它流淌在这个四季分明的纬度。春天的绿芽与冬天的冰雪,或许正是它命定的隐喻。
历史尽管不可复制,但历史总会向前走。古老的沂河,那是我生命脉络的源头,那里有一股细微到不可察觉的气息,有一股相关生命往事的持久传递。那里面有收获,有喜悦,有疼痛,有爱,有眼泪,有别去离伤。那里面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那力量持续延伸到所有的事物之中,那力量持续延伸到有生有情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