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自网络)
N511.冯春明:回望北寨

真想不到,我读中学时的《中国历史》课本上,那幅“豪强地主田庄粮仓图”的出处离我这么近,它竟然就在我的出生地——山东省沂南县城西山背面一个村庄的地下。
在这片看似安静的土地里,深藏着一座用大块青石砌成的“地下宫殿”。这是一座汉墓,它的上面那片肥沃的冲积平原,泥土细腻而深厚。这座“地下宫殿”所在的北寨村,就在碧波荡漾的汶河东岸,它的东面是一座呈如意形状的山脉。这座被视为县城依靠的山,它的北首像似这片平原的枕头。亘古以来,自西部山区滚滚而来的汶河水,向着这个巨大的“枕头”猛烈地撞击之后,迅速调头向南。或许是来到这里的河流,发现自己不该按照头脑里的逻辑横冲直撞,所以它必须依顺着这个“枕头”的指令,以一种持久恒长的力道,年复一年地滋润着这片土地。北寨汉墓则以应有的寂静和安然,处在依山傍水的状态中。这里也因而被人们视为风水宝地。
在这座地下宫殿内,那些用大块青石做成的立柱、横梁、门框、门墩、门楣,以及四周墙壁上雕刻的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石刻汉画像,令人感叹不已。我读中学时,课本上出现的那幅豪强地主田庄粮仓图,就是北寨汉墓画像丰收宴享图的收租部分。这幅画像上画有粮仓、粮堆和几个正往口袋里装粮的仆人。仆人后面是督粮的管家和装满粮食的牛车。整幅图呈现出一种农业丰收后的繁忙景象。课本中,这幅图画虽然是以“反映阶级关系的面貌”出现,但画面上人们杀猪、剥牛、滤酒、烧火、洗菜的场景,却有一种温润和谐的色调。
北寨汉墓是东汉时期的一座墓葬。有专家认为,它是东汉初期伏湛之墓。伏湛何人?伏湛曾两次被光武帝刘秀封侯,建武三年被封为阳都侯,建武六年被封为不其侯。伏湛所处年代,西汉渐趋崩塌,东汉开始崛起。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一切,与北寨汉墓画像中战争场面和生活场景相吻合。作为名儒之子的伏湛,西汉时曾传承父业,教授生徒数百人。西汉成帝时,伏湛任博士弟子,并担任过平原太守。进入东汉后,伏湛是前朝官员中唯一受到光武帝两次封侯的一个人。伏湛作为西汉旧臣,又是东汉时受封阳都侯的一个人物,如依专家所论,这座坟墓是伏湛之墓的话,汉墓画面中的某些场景,应该含有西汉时期的一些元素。
北寨汉墓——当地人称其“将军坟”。相关资料记载:“此墓过去封土很高,犹如土山,顶上长有合抱大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考古专家对其进行发掘。北寨汉墓由前、中、后三室及侧室构成,总面积为88.2平方米。汉墓室内布置均衡,石室由多根八角石柱擎起。大跨度的石过梁,抹角结构的藻井,相互贯通的石室和墓门、墓道,以及酷似近代厕所的蹲坑,实属罕见。而且,在墓门、室壁、柱、础、斗拱、门额,枋子上,全都雕有画像。画像石共有42块,73幅,画像总面积442平方米。这些画像分别刻有朝仪、宴饮、舞乐、狩猎、战争等画面。整个画像气势恢弘、刻工细腻、栩栩如生。
在汉墓墓门上方十分显眼的地方,是一块横幅画像石。这是一幅胡汉战争图,图中有一座桥,桥上和桥右有众多手执刀、盾、矛、斧的汉代步、骑兵,他们由右向左冲锋。桥的左边,有众多手执刀、盾、箭的胡骑、胡卒,他们翻越层层山峦,与汉军在桥头激战。画面上,那些穿越时空,一个个充满血性的人们,从历史的尘烟中走来,他们让我真切地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的碰撞交融中留下的悲壮记忆。渐渐地,我的心情变得沉重了起来,那一组组画面,仿佛就是我们自己的过往。眼前这个战鼓擂动、云烟漫漫的场景中,那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和冲锋喊杀的阵势,似乎早就深藏在我们的身体里,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镶嵌在我们的记忆里了。它太过熟悉,它很容易让人沉浸在对历史过往的回忆里。
再看画面的下方,则是另一番景象。那座正在厮杀着的桥的下边,有一个划船的捕鱼人,他正在安静地劳作。近在咫尺的战争场景,仿佛离他十分遥远,甚至远得遥不可及。再看图下墓门时,但见墓门的三根门柱上,有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及羽人、玉兔、蹶张、仙人、异兽等护佑其间。如此画面,让我强烈感受到人类生存的内涵。人世间所有的一切,仿佛有一缕息息相通的脉络把古今连接。那是一个恢宏的画面,那是被历史所规划,非个人所能把握,牵扯到每个人的生死存亡,谁也躲闪不开的宏大场景。
这里,北寨汉墓墓室主人的具体身份已不再重要,无论墓室主人是否是胡汉战争图里的当事者,还是其他画面里的参与者,那车辚辚、马啸啸的历史瞬间,那桥下安静劳作、生活的画面,已经以一种血性和悲壮,以一种对于生活的热爱和体验,悄然渗透到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里了。那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的存在,又是一种魂魄样的存在,它与我们这个民族如影随形。
历史从来没有静止的存在过,一切都是瞬息万变。但是,这些过往的一切,却始终以一种记忆之流的形式,保持着生命整体的连续性。北寨汉画像石墓中,那一个个历史的场景,距今已近两千年的时间了,它以一种历史切片的形式定格在地下的石头上。它为我们回看自己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画面。现实中,我们很容易把自我与历史割裂开来。就人的生命而言,无论如何变化,无论如何消逝和再生,它也是一个精神性的整体。记得前些年,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这样一段话:“我坚信一旦远离历史的飞轮,生命便不再是生命。”是的,人类生命进程中经历的所有风风雨雨、喜怒哀乐,始终以一种记忆之流的形式流淌在人的血液里。从人类的整体性而言,活着的我们,其实从未死过,否则我们不可能活在现在。
北寨汉墓第二组画像,刻在四壁、立柱、斗拱、过梁及室顶。这组画面以刻于东壁、南壁和西壁三幅横额的吊唁祭祀图为中心,刻出了墓主身后的哀荣。显然,墓主人非常看重自己的地位和荣誉,同时,也清楚每个人总有一天要不可避免地结束人生的旅程。人,当然不希望自身生命局限在有限的今世,也就不断地引伸出许多对于死后世界的想象,墓的主人也不例外。人类从远古开始就没把自身生命局限于“现在”,他们的目光一直向着“明天”展望。基于此,人类生命长河中持续跃动着的那颗灵魂,毫无疑问地成为生命存在的依据。也正因为如此,灵魂贯穿于人的生命过程中,概括了生命问题的全部。
苍茫时空中,人的死亡和降生,很像是一次次生命的接力。而这种接力所传承和交接的恰恰是人的灵魂。人的生命如同每年一度的花开蝶舞,它持续绵延着一种不变的永恒。墓的主人也是一样,他并没有常住在他的地下宫殿里,他就在我们的人群当中,并始终影响着我们的言行举止,影响着我们的情感和情绪,并且与我们一起,一再重现着让我们感到似曾相识的那些“其人其事”的面貌。
数千年来,人类生活中遗留下的每一个脚印,每一个瓦片,每一个痕迹,都是我们辨认思考自己时最为直观的依据,也是我们那个曾经的自己,一次次留下来的不断创造的物证。历史的长河中,许多时候,人们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个选择,或者突然而来的一个念头,甚或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常的事情,它们常常于有意无意间成为历史的亮点。
东汉初年,北寨汉墓旁,匠人锤起凿响,阳光缓缓西移,昼夜不断交替,渐渐地,北寨汉墓光滑的石头界面上,一种奇诡辉煌的生命艺术开始显现了。这种以艺术的形式,取代秦和秦之前残忍的人殉制度,所放射出来的人性光辉,照亮了历史的时空,它让整个汉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闪光点。

(图片源自网络)
北寨汉墓画像第三组为中室画像石。南壁、上横额的西段和西壁、北壁、上横额,是由四幅画面连接在一起的车马出行图,它在北寨汉墓画像中最为壮观。图中,宅院里众多的亲朋,双阙前庞大的车骑队伍,宅院的建筑和车骑队伍后的送者,让人看到了汉时的繁盛和大气,更让人欣喜地发现,在农耕文明的汉代,人们不仅可以将多余的财富和精力用来做一些文明等级更高的事情,而且有许多做到了极致。
且看东壁横额上的乐舞百戏图:众多伎艺人在表演飞剑跳丸、顶橦、走绳、七盘舞、鱼龙曼衍之戏、车戏、马戏,以及敲击钟、鼓、磬、铎,吹奏排箫、笙、竽、埙和抚琴……这其中,人的潜能的发挥可谓古今叹为观止。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发行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币,六枚金币中,第一枚“马术体育造型”图案,就取之于北寨汉墓“乐舞百戏”中的马术表演。金币画面上,一马飞奔,四蹄腾空。马背上有一男子,他左手执戟,右手抓住马鞍,身体飞离奔马,服饰飘荡飞舞。整幅画像造型夸张,动态感强,美得甚至比历史的过往更加真实。
如今,北寨汉墓在那些数不清的混乱而多变的历史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宝贵的空间。我们惊喜地发现,一位“左手执手戟,右手扶马鞍,身体腾空”的男子,从遥远历史的地下一跃呼啸而来。那男子离我们很远又很近,它的影子隐于我们的身体,又远超于我们的肉体。那或许就是我们的魂。
人是不能没有灵魂的,但现实中的我们,却容易在物欲中迷失和沉沦。若谈信仰的缺失,我们缺失的往往是灵魂。回望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从四足着地到逐渐站立的过程中,慢慢地演变而来的。然而,当我们于旷野雷鸣中顽强地站起,并起步狂奔时,那是何等的壮美和欢腾啊!从此,那个颤巍巍地站起的身影,成为我们心灵深处一种超乎时空的存在,一道贯穿始终的风景。
汉代的崛起,无疑是我们这个民族引以为傲的巅峰之一。我们发现,这里有一场深厚博大的心灵与旷远苍茫的历史和自然的交集。北寨汉墓墓室中,上横额下,四周的9幅18个历史故事图和历史人物图,仓颉造字、卫姬请罪、尧舜禅让、周公辅成王、蔺相如完璧归赵、晋灵公纵犬咬赵盾、孔子见老子、荆轲刺秦王、聂政刺韩累等饱含激情、灵动和智慧的故事,应该是墓主人生前津津乐道的。故事中的圣贤豪杰,是墓主人生前景仰的人物。不难想象,这里有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潜藏其中。
汶水滔滔,青山作证。北寨汉画像石墓,规模宏大,墓室结构复杂,画像雕刻精美,内容极其丰富,俨然是一座庄严肃穆而又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地下府第。北寨汉墓画像直抵人的内心,让每一个人都无法置之度外。它既是汉代生活的一个缩影,更是我们回望自己的一面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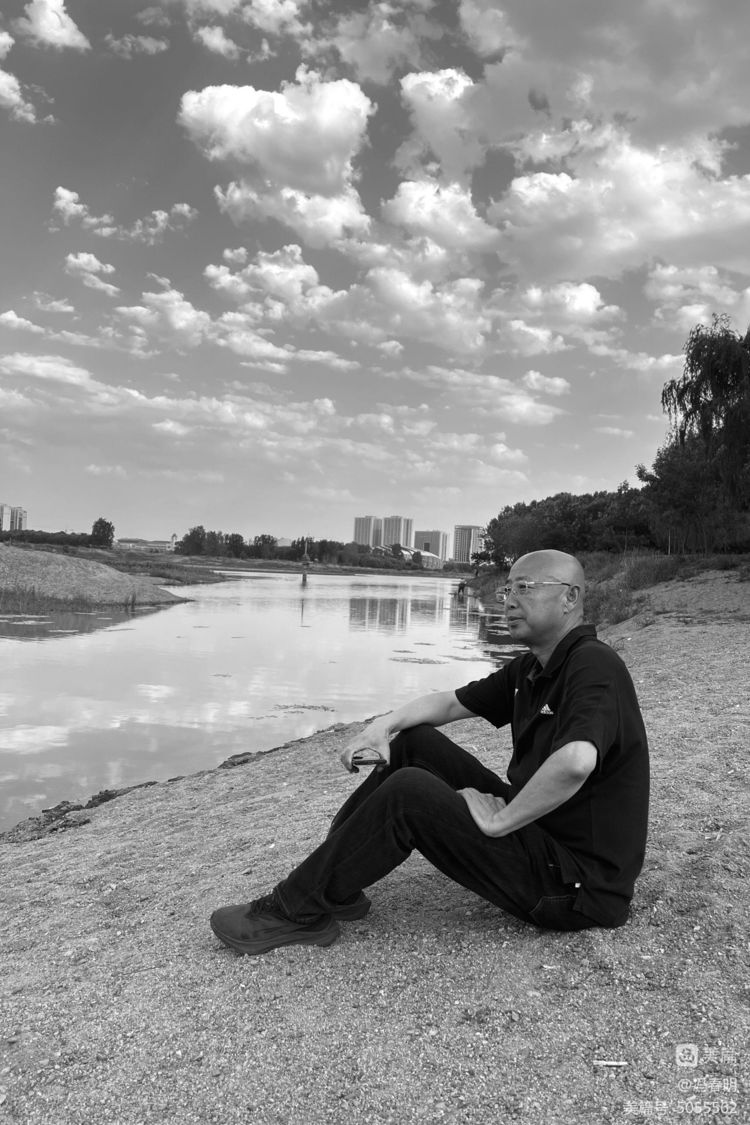
冯春明,1959年生,山东沂南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有散文、文学评论见于《山东文学》《山东作家》《前卫文学》《时代文学》《当代文苑》《青岛文学》《延河》《九州诗文》《莲池周刊》《时代报告》等。著有散文集《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