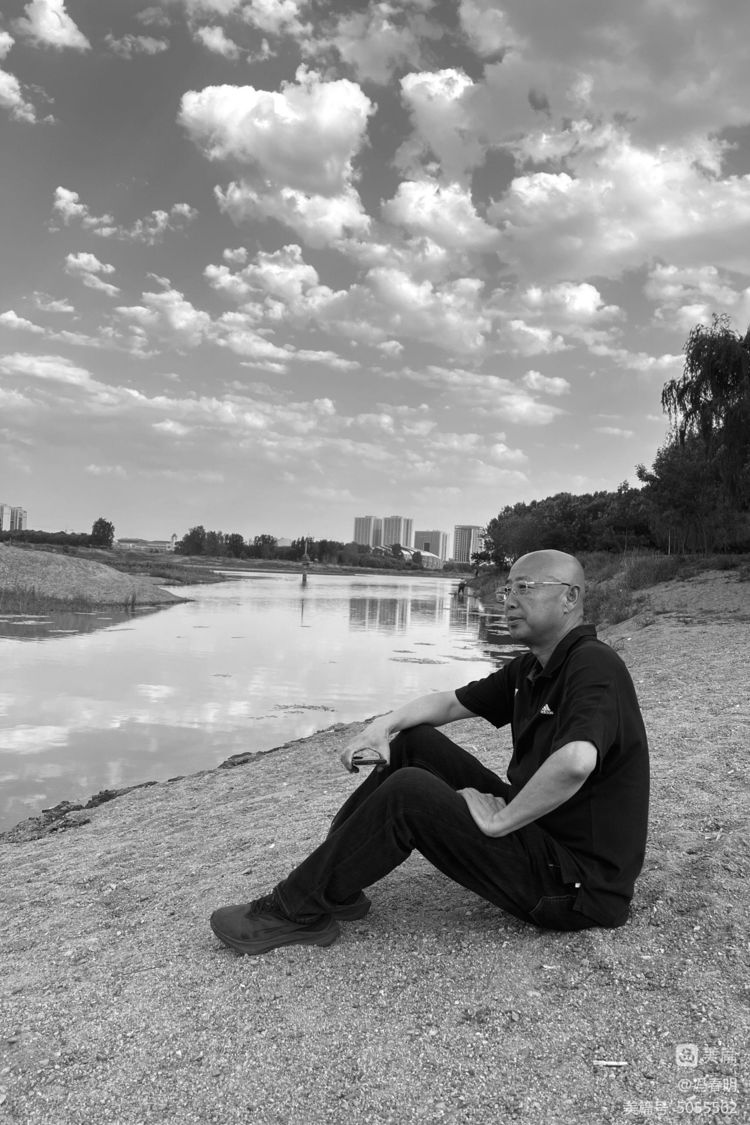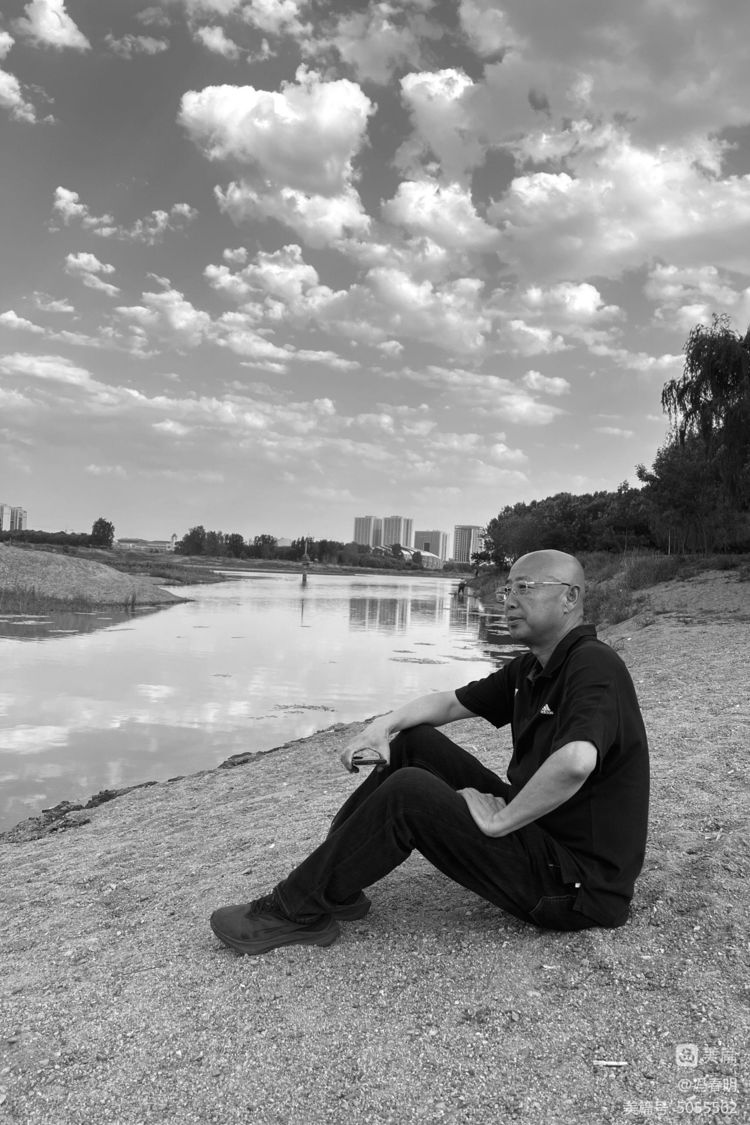2023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沂南县蒲汪镇中心小学刘庆伟校长,把我和同行的文友们领到圣母联小校区后边一块实验田内,我在两块有着不同品种的南瓜地里,摘了两个扁圆形的南瓜。南瓜在青一色的南瓜秧上长大,一位老师用手帮我扶住粗壮的秧梗,我双手捧住南瓜,轻轻一扭,咔的一声,摘了下来。两个南瓜,一个橘红色的,一个青色的。南瓜个头不大,却长得结实。刘校长告诉我,这是学校老师和孩子们课余时间栽的。现在,放学后的孩子们,可以摘上自己亲手栽培的南瓜,带回家给爸妈尝一尝了。
N510.冯春明:蒲汪中心小学,一所脚踏实地的学校


刘庆伟校长是个有心人,他在校园里专门为孩子们留出了一块地。在这块土地上,孩子们可以种瓜、种豆,可以浇水、施肥,可以看着种子发芽、幼苗生长,花开花落,直到陪着瓜果长大。在这片南瓜地里,孩子们踏在地上的小脚丫和伸向这块土地上的一双双小手,就像小树的根系那样扎进了这片土地。在刘校长看来,这些走进校园的孩子们,只有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深深地扎下根来,才能长成接地气的孩子,以后不管走到哪里才能让人放心。
校园原本就在土地里。人类进入农耕文明后,长辈们在田野里指导晚辈们如何播种,如何施肥、除草、除害,如何收割,如何储存种子……这便是人类最早的课堂。直到孔子教授生徒时,课堂也大多在路上。现代化、信息化的今天,是否意味着教育就要告别土地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今天,我和众多文友们为参加蒲汪中心小学“新芽文学社”揭牌仪式而来,想不到,走进校门之后,竟然有了许多出乎意料的收获。蒲汪中心小学让学生“动脑、动腿、动手、动嘴,一起动起来”,“因人施教,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教学实践和“教书育人”的理念,让人印象深刻,大有耳目一新之感。
丽日当空,蒲汪中心小学院内南北通道上,两位学生讲解员引领我们来到楼下过道内,在两位学生记者的现场直播下,参观了孩子们做的蛋壳雕塑。这是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利用阴刻技法在蛋壳上创作的艺术品。这些童真稚拙、谐趣活泼的作品,从凿壳、清洗到雕刻,每一个环节都不得马虎,稍有不慎或差池就前功尽弃。这正是刘校长和老师们想要的。当看到孩子们屏住呼吸,集中精力,一刀一刀地雕刻着薄薄的鸡蛋壳时,他们开心地笑了。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孩子们的定力、平衡力、脑与手的配合能力,得到了全面锻炼和提升。课堂上,孩子们更能静下心来听讲了。
今天,刘校长领我们去了三处联小。每个联小各有特点。课余时间,学生们转呼啦圈,跳绳,吹口风琴……他们个个精神饱满,十分活跃。用刘校长的话说,这叫“一校一品”。“一校一品”这种尝试,从去年秋天开始。学校在没有专业老师的情况下,联小老师们靠自修、自研、自学,边学边教,半年下来,效果远超预期。
“一校一品”是刘庆伟校长在没有专业老师,没有现成经验可取的情况下,一个具有可行性的尝试。蒲汪中心小学通过“一校一品”的实践和经验积累,很快就可以全校开花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教会了孩子们音、体、美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使孩子们得到全面发展,老师自己也成为老师中的老师。




图书室是刘庆伟校长为孩子们倾心打造的读书平台,每一个联小的孩子都有机会来图书室读书。在中心校走廊,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四五年级的学生,他通过老师找到我,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诗经》是怎么成书的?二是《长恨歌》的题目里为什么有一个恨字?这个孩子的提问让我吃了一惊,这么小小的年纪,心里竟然装着如此宏大而深沉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给孩子做了常识性的回答。第二个问题我告诉孩子《长恨歌》题目里的恨字需要从诗的内容里去寻找。孩子说,这个恨字……孩子稍一停顿,然后,略有所思地说,唐玄宗、杨贵妃爱情的恨……他又一停顿,好像在说,不是。这时,站在一旁的老师说:“还有亡国之恨。”我跟孩子说,你能了解这些,尤其能想到这些,已经难能可贵了。当然,就我个人观点而言,《长恨歌》的作者白居易,他的那个“恨”字,恨的不是别人,他恨的是自己,恨自己无力回天。古代中国文人啊,他们的肩膀尽管不宽,但是他们骨子里的那种家国情怀,那种担当,不是人人都能够理解的。不过,提出这个问题的孩子,我觉得他似乎开始思考这个方面的问题了,甚至比我想得更远。过后,老师告诉我,这个孩子经常去图书室读书,读了很多书。
来蒲汪中心小学不到一天的时间,却收获多多。回家后,因为急着整理我的散文集,没有来得及动笔,今天看到很多文友们已经把文章写出来了,心里急得慌,先草草来它两笔,权作交作业了。
在此感谢蒲汪中心校刘庆伟校长和各位老师和各位亲爱的孩子!祝福你们。
冯春明草
2023.6.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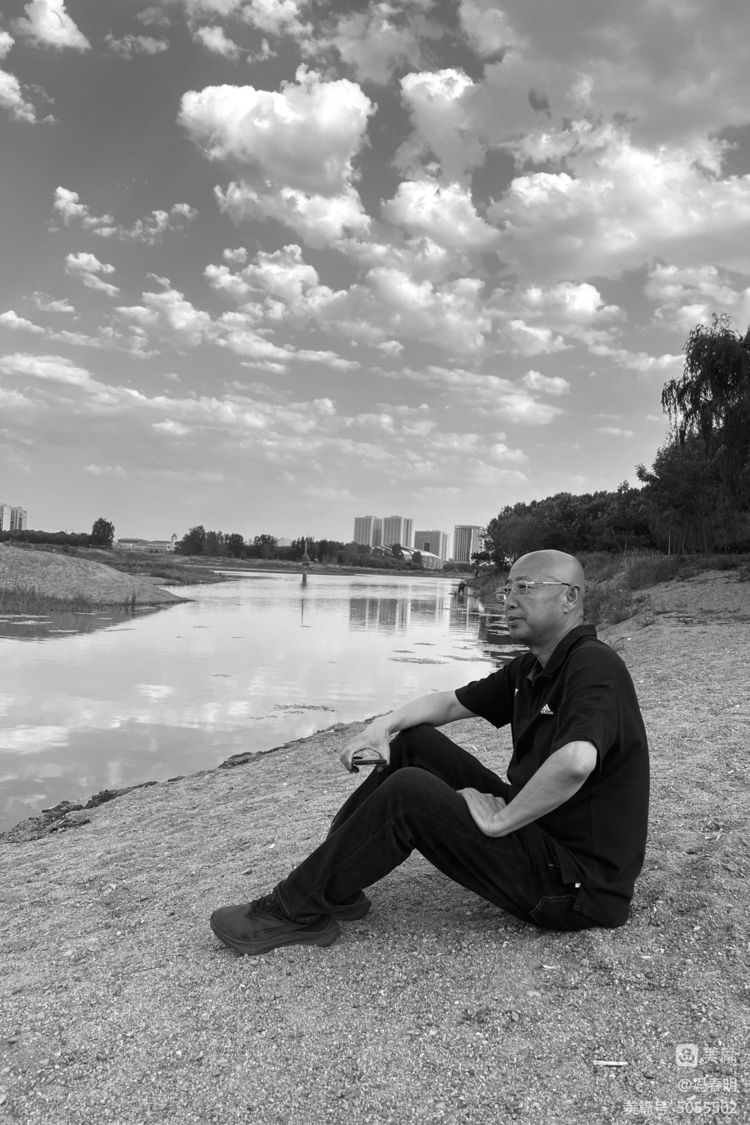

冯春明,1959年生,山东沂南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有散文、文学评论见于《山东文学》《山东作家》《前卫文学》《时代文学》《当代文苑》《青岛文学》《延河》《九州诗文》《莲池周刊》《时代报告》等。著有散文集《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