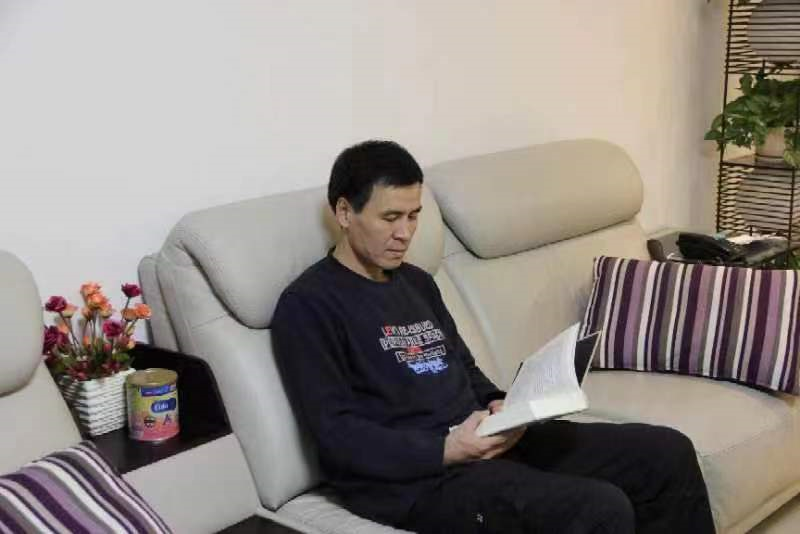N516.冯子栋:兴佛庵,一座少为人知的神秘寺院
群山重重,屏蔽了远方的喧嚣。 丛林深深,湮没了历史的风烟。 我驱车赶往沂水县夏蔚镇上桃峪村,去探访一座神秘的寺院——兴佛庵。 群山绵延,如一道道绿色的海浪向车后退去,又从前面涌了上来,“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群山用它们的坚实与伟岸层层屏蔽着远方的喧嚣、浮华,越往里走越自然、淳朴、安宁。 蜿蜒前行二十里后右转向北翻过一个陡坡,左方山坳赫然出现一排崭新的居民楼,五座五层,白墙红顶,宛如一艘巨轮从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驶来,乘风破浪,格外醒目。没想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春风竟吹到了大山深处,在这里开花结果展新颜,令我感到一阵惊喜和振奋。 几位老人正坐在树荫下聊天,脸上都洋溢着亲切、幸福的微笑。 我举目四望寻找兴佛庵,却找不到挑角飞檐的古楼建筑,也听不到佛韵悠扬的钟声梵呗。我一脸茫然,兴佛庵到底在哪儿呢?一位五十来岁的大哥热情地带我走到村南的一条小路旁,指着西山说:“这山叫凤仪山,沿这条小路一直走到半山腰,然后左转往里去就能找到兴佛庵。” 夏天的一场场暴雨早已把进山的羊肠小道冲成了小水沟,茂密的足有一米高的荆棵把小路遮掩得若隐若现。一串串细碎的荆花正次第开放,为翠绿色的山野点缀了星星点点的紫色,清新、淡雅的荆花香味在空气中缓缓荡漾,数不清的蝴蝶闻香而来,在荆棵丛中翩翩起舞,翅膀开开合合,为这些远离喧嚣、默默绽放的生命之花鼓掌喝彩。 当我在丛林深处的小道边蓦然发现一块写有“兴佛庵”字样的黑色大理石时,不由得心头一振,便疾步趋前。右前方是一段东西约三十米长的悬崖峭壁,峭壁上有一个约一米见方、不知凿于何年何月的神秘佛龛,里面所供奉的佛像早已不知去向,空空如也;崖下有两个天然棚状石洞,崖前则是一片被乡亲们种了庄稼的断壁残垣,再往前便是陡峭的山坡和茂密的山林。 传说北宋年间,有一位大德比丘尼来到这里,广募善缘建成此庵。她许下宏愿:兴佛弘法,普度众生,为黑暗中的乡亲点亮心灵的明灯。 来这儿之前我曾多次想象过兴佛庵的模样——一个挑角飞檐、古韵悠悠、佛香袅袅的伽蓝寺院。而眼前的场景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心向往之的兴佛庵竟已成为荒草丛生、无人问津的断壁残垣。从现场遗迹可以推断,这里不曾有规模宏大的挑角飞檐,不曾有富丽堂皇的庭廊殿堂,不曾有佛事鼎盛的辉煌过往,仅仅有过几间简陋而狭小的石屋、石洞而已。曾经的经声梵乐早已消逝在历史的长空,曾经的佛庵小院早已被岁月的风沙掩埋,曾经的功德碑林早已散落在地坝、小路上,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埃,空空寂寂,尽显岁月的悲戚与苍凉。 站在兴佛庵的断壁残垣间,我看到六百多年前一个匆匆而来的身影。 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夏天,一队战马如离弦之箭疾驶在通往凤仪山的山道上,急促而沉重的马蹄声打破了黄昏的宁静,布谷停鸣,群鸟惊飞。一位身着红袍、英锐庄严的年轻女子跳下马,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了兴佛庵…… 这位年轻女子正是明初著名农民起义军首领唐赛儿。 自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靖国难”的幌子发动靖难之役,攻占南京篡夺其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帝位后,开始忙着为迁都北京做准备。大兴土木建造故宫,征调数万民夫疏浚京杭运河,赋税徭役逐年增加,再加上连年灾荒,百姓苦不堪言,积郁已久的民愤随时有被点爆的危险。 唐赛儿自幼习武,侠肝义胆,受其母亲影响信奉白莲教,广结善缘,声名日起。1419年,她的丈夫林三在疏浚京杭运河时因看不惯监工的飞扬跋扈而发了几句牢骚,被残暴地杀害。唐赛儿悲痛欲绝,多次与父亲到官府申冤,要求缉拿凶手,官府却推诿扯皮、置之不理。不久后她父亲悲愤而死,母亲也重病身亡。家庭的一系列变故给唐赛儿带来了沉重打击,也加深了她对官场酷吏的仇视和痛恨。在正义得不到伸张的至暗时刻,奋起反抗是最无奈、最悲壮的绝唱。1420年,唐赛儿带领几千名白莲教饥民在青州缷石棚揭竿而起,他们从青州打到莒县、即墨,斩杀青州卫指挥使高凤,诈降大败安远侯柳升和都指挥使刘忠,毁官衙,开粮仓,济灾民,名震朝野,令明成祖朱棣寝食难安。 当起义军围攻安丘时,朱棣急调抗倭名将卫青飞兵解围,战场形势由此发生逆转,起义军腹背受敌,死伤惨重,溃败。千钧一发之际,几名侍卫为唐赛儿杀出一条血路,马不停蹄三百多里来到了凤仪山下,走进乡亲们的心灵圣地——兴佛庵。 凤仪山如慈悲的佛祖,默默注视着疲惫不堪的唐赛儿,伸开宽大的臂膀将她收入怀中。从此,唐赛儿隐姓埋名,在青灯古佛下诵经打坐,面壁参禅,过着清静而简朴的佛家生活。 深山藏古寺,明月照清心。在这偏远、幽静、庄严、肃穆的丛林道场,唐赛儿放下斩妖除魔的刀兵,放下嫉恶如仇的执著,听晨钟暮鼓,沐清风鸣蝉,望苍穹明月,悟佛法禅机,疲惫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所有的愤怒、仇恨、抗争、杀伐如乌云般渐渐消散…… 朱棣下令悬赏搜查江北所有寺庵,挖地三尺也要找到唐赛儿,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唐赛儿音信全无,像空气一样从人间蒸发了,成为他的终生遗憾。朱棣哪里知道,在朴朴实实的乡亲心里,唐赛儿是不畏强暴的女中豪杰,是圣洁慈悲的住世佛母,她勇于反抗、伸张正义的精神令百姓由衷钦敬,人们宁愿冒着被杀头、株连的风险也要把她藏在这“远在深山少人问”的丛林兰若之中,世世代代守口如瓶。正因为唐赛儿的到来,注定了兴佛庵在远离喧嚣的群山深处渐渐走向沉寂。 山谷幽幽,林木苍苍,数不清的树冠连成一片,像一张巨大的华盖为凤仪山遮风挡雨,又像千千万万的乡亲一样默默守护着兴佛庵。一阵山风吹来,声势浩大的风涛掠过树冠,轰轰作响,如排山倒海,像狮吼虎啸,似万马奔腾,大有气吞山河的磅礴之势;而林中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树影斑驳,流水潺潺,氤氲着清凉、静谧、安然的气息。 唐赛儿起义给了朱棣一次当头棒喝,令他猛然意识到苛政猛于虎的重大危害。为稳固政权、平息民怨,他先后惩治了一批贪官酷吏,颁布了一系列赈灾、轻徭薄赋的诏令,大大缓解了官民对立的社会矛盾,为大明王朝开创了一个政通人和、河清海晏的盛世新局。 唐赛儿圆寂后,到了明万历年间,有一位叫任静安的僧人在此开耕种田、续佛弘法。 又过了三百七十多年,中国进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斗志昂扬的红卫兵冲进兴佛庵,把这座象征牛鬼蛇神的千年古刹砸得伤痕累累…… 眼前的断壁残垣令扑朔迷离的历史变得更神秘莫测,残缺不全的碑文如奄奄一息的老人在含糊不清地诉说着那些零零碎碎的往事。六百多年前的金戈铁马已化为乌有,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场景已成为永不再现的传说。 走进石洞之中,清爽、潮润的气息扑面而来。嶙峋的洞壁上长满了绿绒绒、鲜嫩嫩的青苔,宛如一幅丹青涂染、千峰竞翠的山水画卷;一条晶莹如练的清泉从洞壁罅隙中流了出来,注入一方清澈见底的石潭之中,哗哗哗哗,清泠悦耳,激起一圈圈大小不一的涟漪。泉水出潭而去,携着高山的质朴、森林的清新、土地的醇厚,冲过一道道堤坝、一座座石桥的阻拦,头也不回奔向山外的远方。看着泉水欢歌而去的身影,我蓦然想起白居易写的那句“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泉水多么像儿时的我们啊,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可阅过千山万水之后却发现最美的风景竟是那永远回不去的童年。我想,从腥风血雨中走来的唐赛儿看到这清冽不染的泉水时,是否也会想起这句诗?转念又想,大彻大悟后的唐赛儿是否又是另一种感受:“流水下山非有意,片云归洞本无心。人生若得如云水,铁树开花遍界春。” 站在清凉、幽静的树荫下,透过斑斑点点的枝叶缝隙向外望去,远远近近的山峦层层叠叠,氤氲着一层薄薄的雾纱,杳霭流玉,袅袅婷婷,宛如一条圣洁的哈达,拨慢了时光的钟表,让生活的脚步停了下来。 绿水青山,布谷声声,崭新的居民小区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安宁,人们沉浸在新时代的幸福生活之中,有关兴佛庵的那些往事已随风消逝。 作者简介:冯子栋,山东蒙阴人,在临沂河东农商银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