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66 冯子栋:散文 | 大慈恩寺,闪耀着垂范千秋的人性光辉
山东金融文学 2024年09月20日 00:00 山东
我随着潮水般的人流缓缓地走向大慈恩寺。
宽阔的街道两侧是粗壮繁茂的古松、国槐,宛如一位位身着宽袍、双手合十的高僧,为远道而来的众生捧起一方清凉、安宁的心灵净土。从树上垂下来的一张张印有优美诗词的卡片,随风飘舞,如欢蹦乱跳想极力挣脱怀抱的小精灵。石林中那些一人多高的石柱上刻有一首首意境闲适的田园诗,还有灯箱、公交车厢、站牌上那些随处可见的诗词,彰显了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清新、优雅、禅意的文化底蕴。许多年轻姑娘穿着汉服,薄衫长裙,金簪玉坠,步摇流苏,像翩翩起舞的蝴蝶一样穿梭在人流之中。
当我走进大慈恩寺的时候,大唐王朝的两位帝王从历史殿堂里向我款款走来……
公元636年,时为晋王的唐高宗李治才刚刚九岁,他的母亲文德皇后突然病逝,从此,这个世界上最疼他、最爱他的人走了。身处皇宫的他倍感孤独与无助,时常怀念与母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母亲的美丽、慈和、严厉、节俭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成为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风树之切,刻骨铭心,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双手手心特别疼痛,他固执地认为,那是母亲的在天之灵对儿子捧心之痛的感应。
公元648年,身为太子的李治奏请父皇太宗在京城建一座寺院,弘扬佛法,广结善缘,为母亲的在天之灵追荐福业。
太宗皇帝又何尝不怀念那个曾与他相濡以沫的文德皇后呢?这位“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的天子,也是一位体国爱民、广开贤路的明君。他的成功,离不开文德皇后生死相随的陪伴与支持。他十五岁那年,与十三岁的她情定终生,一双两好,走过风花雪月的浪漫,经受腥风血雨的洗礼,从青梅竹马到举案齐眉,书写了忠贞不渝的爱情。他君临天下后,贵为皇后的她仍然保持着温厚节俭、与人为善的本色,深得群臣、宫人的敬重。为了大唐社稷的长治久安,她向性格刚硬的他建议重用魏征、房玄龄、褚遂良等贤臣名士;为了防止外戚权力泛滥,她提醒他慎用她的哥哥长孙无忌。在她春风化雨般的启发影响下,他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开创了政治清明、流传千古的贞观之治。她离世后,宫女把她生前编写的一部以记录古代妇女美德故事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女则》呈现给他,她在书中提醒自己一定要汲取汉朝马皇后干政的惨痛教训,不给他添乱,做他的好妻子、贤内助。这源自内心深处的真诚,深深打动了他,他动情地说:“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在他眼里,她就是万古流芳的“女则”!她离开他已整整十二年了,为人忠厚的皇儿李治要为她建一座寺院,孝心可鉴,他深感欣慰,立即准奏。
太宗皇帝在皇儿李治身上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两人的情感境遇是何其相似啊!他的母亲太穆皇太后和文德皇后一样,也是一位仁和达理、母仪天下的女人,他结婚那年,母亲离他而去。那时,他也和皇儿一样思母心切,在长安为母亲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弘福寺,迎请大德高僧驻锡弘法,护佑母亲的在天之灵。
当李治把破落不堪的净觉古寺改造成长安规模最大的寺院时,太宗皇帝亲自为其题名“大慈恩寺”,大爱慈悲,恩泽千秋。这座焕然一新的寺院,寄予了太宗皇帝对文德皇后的深切怀念,也寄予了太子李治对母后的殷殷感念之情。太宗皇帝恭迎玄奘法师和五十位大德高僧驻锡大慈恩寺,并为他们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入寺升座仪式。太宗皇帝认为,有了众多高僧尤其是玄奘法师的慈悲加持,文德皇后的在天之灵必会得到无量的护佑,她的贤淑美德也必会垂范千秋。
家国天下,忠孝为先。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寻常百姓,唯有善良、感恩才让历史的漫漫长空变得更加明亮,让人类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温暖。太宗皇帝认为:心和,家和,方能天下和。这深得民心的“以孝治国”理念,深刻影响着高宗皇帝,他温厚仁和,勤政爱民,在父皇贞观之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创了政通人和、官顺民敬的永徽之治。
从弘福寺到大慈恩寺,见证了两代帝王对两位母亲的蒸蒸感念之情,也见证了两位母亲对大唐王朝国运的深远影响。
一座七层方锥形楼阁式佛塔,从古树掩映的大慈恩寺北院脱颖而出。赭黄色的塔身,青灰色的塔檐,每层四面各开一个拱形小门,塔顶是三重宝葫芦状塔刹。这座古朴、典雅、庄严、神秘的七级浮图,就是古今闻名的西安地标式建筑——大雁塔。
说起大雁塔,无论如何也绕不过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唐僧。
我们对《西游记》里的唐僧是再熟悉不过的: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骑着白龙马,靠三个徒弟斩妖除魔到西天取经,除了会念几句咒语外,似乎也没多大能耐。而我们对唐僧的原型——玄奘法师却知之甚少。玄奘法师是一位真正靠自己的学识、德行、毅力赢得帝王、学者及无数僧俗为之钦佩、景仰的高僧。他从小就聪慧颖悟,十三岁就胸怀“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远大志向,被破格剃度为大唐王朝年龄最小的僧人。他十九岁那年从洛阳出发,徒步游学到长安、汉川、成都、荆州、扬州、吴会、赵州、相州等地,后又返回长安,历时八年,行脚近一万公里,先后受教于十三位佛学大师。他学识日渐渊博,能把玄奥繁杂的经文讲得头头是道,其出类拔萃的记忆、超群绝伦的口才令人啧啧称奇。博洽多闻的他,风尘表物,已成为大唐王朝最年轻、最博学的高僧。
然而国内的汉传佛教典籍残缺不全,存在许多错讹和疏漏,令玄奘倍感迷茫和困惑。他发宏愿:去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求学,学成回国弘法利生。
在未经朝廷准许的情况下,玄奘偷偷出国,躲过凉州都督李大亮的千里追缉,进入沙海茫茫的八百里莫贺延碛大沙漠,几度昏迷后绝处逢生;翻越终年积雪、陡峭难行的凌山;两次遇到歹徒,被洗劫一空……
玄奘虽经历了重重磨难,但也得到了许多人的礼遇和厚待。高昌王麴文泰亲自掌灯出城欢迎他的到来,与他秉烛夜谈,做了他的结拜兄弟,并出城送他十里。在外出征的突厥王叶护可汗得知他到了碎叶城,立即赶回行宫为他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请他讲法,并携群臣送行十里。在缚喝国,名闻印度的小乘佛教学者般若羯罗精心指导他学习《毗婆沙论》,并陪他一路游学到千里之外。在迦湿弥罗国,国王亲自把他迎入宫中,给予丰厚的供养,饱读经书的著名学者僧称则毫无保留地为他讲解《俱舍》《正理》《因明》《声明》等经论。
四年后,玄奘终于来到了魂牵梦绕的佛教圣地——摩羯陀国那烂陀寺。这里是印度最高的佛学院,也是印度规模最大的佛教文化交流中心。有一万多名僧人在这里学习深造,学者云集,其中最有学问的是全印度唯一一位能通解全部经论的戒贤法师。戒贤法师德高望重,已一百零六岁高龄,当他得知玄奘独自一人越过千山万水、历尽波折来取经时,被这个年轻人舍身求法的精神、谦逊纯正的品德、坚韧不拔的意志深深打动,特意花了十五个月时间为他讲解大乘佛教的经典教义——《瑜伽师地论》。玄奘心无旁骛地倾听,学完后又认真复习了三遍,茅塞顿开,曾经的缺憾和疑惑一扫而光,对这部经论有了全新、系统而深刻的领悟。他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继续潜心学习其他大小乘经论、婆罗门教典、各类梵书及印度文学,博闻多识,为以后回国译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了整整五年,已成为戒贤法师身边最优秀的弟子,一位大小乘兼识、内外经皆通的集大成者。
面对大乘佛教著名中观派学者师子光宣讲《中论》《百论》时挑起的中观派与瑜伽行派之间的激烈争论,玄奘写了《会宗论》,指出师子光观点的偏颇之处,并多次找师子光辩论,驳得对方无言以对。玄奘得到戒贤法师和僧众的高度赞誉,从此在印度声名鹊起。
赫赫有名的小乘佛教论师般若毱多是一位三代帝王之师,曾写了一篇《破大乘论》攻击大乘佛教,十二年间无人能驳斥他。玄奘认真研读这部经论,了解了般若毱多的论点、论据及破绽,写下了著名的《制恶见论》,以无可辩驳的论述驳斥了般若毱多的观点。大乘僧人视《制恶见论》为不刊之论,争相传阅,交口称赞。当时印度最有势力的一位国王叫戒日王,对玄奘礼遇有加,对他的《制恶见论》更是推崇备至,特意在首都曲女城为他召开了印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佛学辩论大会。参会的有十八位国王、六千余位学者,观礼的僧俗更是不计其数。戒日王亲自主持大会,将玄奘的《制恶见论》悬挂在会场,接受所有学者的驳难。除了前五天有几位学者站出来辩难被玄奘一一驳倒外,此后直到大会结束整整十八天无人再出来发难。玄奘取得了众望所归的胜利,被大乘弟子奉为“大乘天”,被小乘弟子奉为“解脱天”,众星拱辰,名满五印。时至今日,印度的中小学教科书上仍尊称他为“印度史上的一位圣人”。
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十七年,走过大大小小一百三十八个国家,行程五万多里。他靠着执着、坚韧、好学、辩才,在异国他乡赢得了至高无上的礼遇,获得了中国留学生史无前例的荣光,也书写了中国留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
玄奘法师回国后拜谒太宗皇帝,他的学识、修养和所经历的磨难、荣光,得到太宗皇帝的由衷钦敬,两人年龄相仿,相见恨晚,促膝长谈,成为无关名利的莫逆之交、远离庙堂的灵魂知己。
玄奘法师建议太宗皇帝通过广度僧尼来树立功德,太宗皇帝立即准奏,诏令全国度僧一万八千五百余人。唐朝佛教由此走向兴盛。
太宗皇帝尤为关注玄奘法师译经弘法,特意在大慈恩寺为他设立翻经院,亲自为他写了一篇经序——《大唐三藏圣教序》,时任太子的高宗李治也紧随其后写了篇《大唐三藏圣教序记》。正因为有了这父子两代帝王的倾情相助,玄奘法师所翻译的佛经才得以流传得更快、更广。后来,唐朝著名书法家褚遂良将这两篇经序制成碑文,立于大慈恩寺内以作纪念。如今,这两块石碑依然坐落在大慈恩寺内,碑文丰筋通神、玉润雅秀,成为一道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
太宗皇帝在生命弥留之际,默默地看着玄奘法师,安然离世。从此,两个举世无双的王者,两个尊贵高尚的灵魂,一别两宽。
高宗皇帝对玄奘法师始终崇敬有加。玄奘法师奏请在大慈恩寺内建一座五层佛塔,用来保管从印度取来的佛经、佛像、舍利等珍贵物品。高宗皇帝立即准奏,并亲自帮他拟定施工方案。佛塔建成后,玄奘法师将其命名为“大雁塔”。
在古印度有一个关于大雁塔的传说:一群小乘佛教僧人走在路上,已是午后,饥肠辘辘,这时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一位僧人随口说道:“佛祖应该知道我们都饿了吧。”话音未落,领头雁扑通一声坠落在僧人面前,众僧皆惊,认为这是如来佛祖的开示,便在雁落处建了一座塔以表纪念,众僧从此改信大乘佛教。
玄奘法师在大慈恩寺译经长达九年,常常“三更刚眠,五更复起”,平均五天翻译一本经书,速度惊人。大慈恩寺由此成为大唐王朝最重要的译经院之一,也成为中国大乘佛教法相唯识宗祖庭。
公元664年,玄奘法师圆寂,高宗皇帝不胜哀痛,罢朝三天,携文武百官为他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国葬,不计其数的百姓、僧人自发来到长安为玄奘法师送行。其丧礼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玄奘法师一生共翻译了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经书,占隋唐时代译经总数的一半以上,著作等身,数量惊人。梁启超先生称他为“天下第一人”,鲁迅先生盛赞他为“民族的脊梁”,日本佛陀弟子则奉他为“护法善神”。
人世无常,太宗皇帝、玄奘法师、高宗皇帝这些垂范天下的帝王、高僧早已相继作古,最初那座占地约四百亩的大慈恩寺早已在兵燹战乱中废弃,最初那座砖表土心的五层大雁塔早已在风雨剥蚀中坍塌,就连玄奘法师视若珍宝的贝叶经、佛像、舍利子也早已不知去向。眼前巍然耸立的七层大雁塔始建于武则天长安年间,眼前的大慈恩寺则重建于明朝,它们虽几经修建早已不再是当初的模样,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依然承载着那段灿烂辉煌的历史记忆,依然闪耀着两位帝王、一位圣人垂范千秋的人性光辉,依然能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那些穿越时空、催人奋进、引人向善的强大精神力量。
我在玄奘法师高大魁梧的雕像前驻足仰望,他正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取经路上走来,右手执杖,左手施礼,慈和的目光中透着坚毅、威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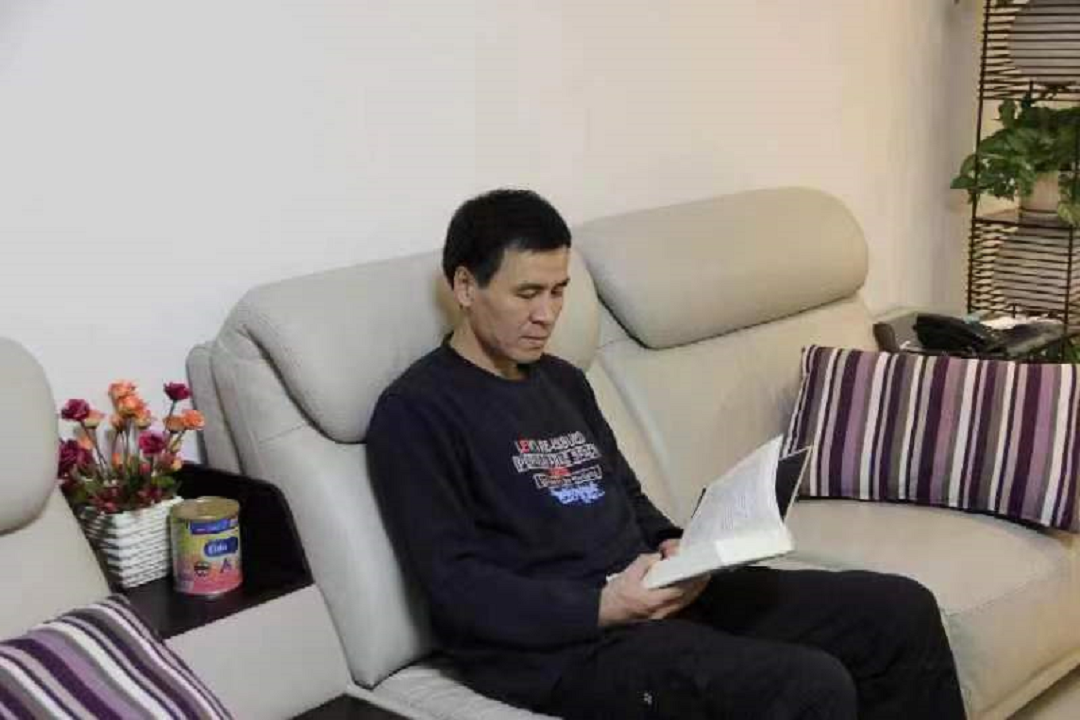
作者简介:冯子栋,山东蒙阴人,现在山东临沂河东农商银行工作。

